一、引子
1985年,谭其骧先生在桂林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对王士性及其著述《广志绎》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王士性对地理学的贡献和徐霞客相比,大致在伯仲之间;《广志绎》的价值,总的来说,可能稍逊于《徐霞客游记》,在人文地理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p.189-200]谭先生以他超凡的睿智和远见,开启历史的尘封,使这位被湮埋达三、四百年的杰出地理学家重放异彩。一时研究王士性的论著不断,成为学界的一个亮点。
1992年,“王士性研究”被列入浙江省“八五”规划的重点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推出了一批厚重的研究成果。其中,周振鹤编校的《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令人瞩目,该书是目前整理和研究王士性主要著述的最佳版本。另一项成果是徐建春、梁光军合著的《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进一步拓宽了王士性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有学者指出:“从重视徐霞客到重视王士性是中国人文科学复兴的一个标志”,“王士性应当是与其同时代的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并列的大科学家。”[2][p.97-100]
目前,王士性研究似乎已成为“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文衡、冯岁平、魏子云(台湾)等学者均就《徐霞客游记》中涉及到的有关王士性的记载,作了分析和论证,找到两位地理学家时空上的交汇点——云南鸡足山,这无疑将进一步推进徐、王的比较研究。[3]
作为布衣以游的徐霞客,及其当年考察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云南,自然受到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但是,王士性在云南的情况,省内学者的研究可以说尚未起步。概因一则王士性为官云南业绩不显,地方志中几无列传,仅在艺文志中得见相同篇目的诗文;二则徐霞客的影响在云南已深入人心(朱惠荣先生更评“徐霞客是云南历史发展的恩人”。[4][p.87])云南学人对王士性的研究尚未留意。时至2001年昆明市志办《史与志》才刊有对《广志绎》(附《五岳游草》)的笔记著录。在该刊2002年第4期上李惠铨先生对《广志绎》的初刻年代进行辨证。[5]而对王士性其人其事其说研究得并不多。
本文透过王士性对滇云史地的考究,结合明代云南历史和文化,试图勾勒出王士性在滇的行迹,研究王士性与云南,并得出几个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仅涉及王氏对滇云史地的考究,关于王士性在滇游踪及宦滇政务述略,另有专篇论及。
二、王士性及其对地理学的贡献
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台州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人,生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入仕,宦及北京、河南、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官至南鸿胪寺卿,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6]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含《广游志》二卷),《广志绎》六卷(实为五卷,第六卷《四夷辑》仅存目),周振鹤辑为《王士性地理书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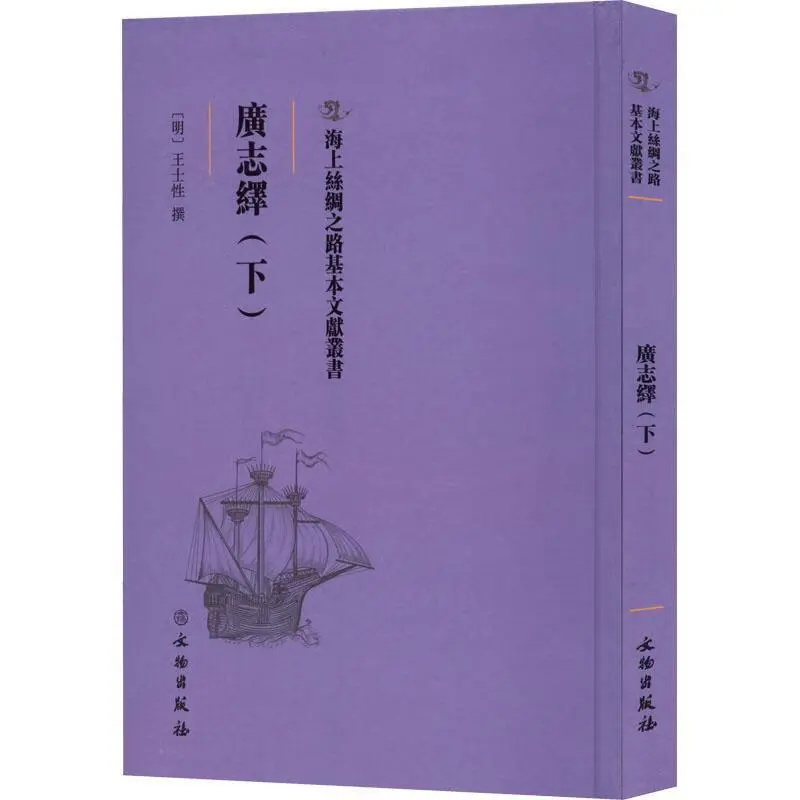
王士性为官二十一年,“宦辙所至”,[7][p.234]遍游五岳兼及各地名山大川,除福建未到外,其余两京十二省均留下他的足迹。四十年后,以“游圣”著称的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8][[p.890,1179]可见对他的推崇。
王士性每到一处,都十分留心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交通漕运、地理形胜、民间习俗和人民疾苦,注意研究各地社会文化的差异,见解独到。正如周振鹤指出:“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开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来,其后长时间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9][p.12]
学者们还研究得出,王士性早黑格尔两百年便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人地关系思想,尤其是他将浙江分为浙北、浙西和浙东地区,根据地形地势的特点,划分为平原水乡、丘陵山区和滨海区,精辟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生活于其间的居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让人惊叹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同一性。王士性还具有宏观的兼及各地地理差异的区域思想和顾炎武著作抄录所反映的“郡国利病”、经世致用的地理学思想等,指出他对地理事象进行的一系列理性思索,而不仅仅忠实地记录,是他较徐霞客尤为可贵的地方。[10]
王士性对天文、气候、地貌、山川等自然环境也多有涉及,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仅从“(案:《广游志》卷一《地脉》《形胜》《风土》)短短三节之中,论述我国主要地区山脉的分布,各省的形势,以及局部的气候,提出于将近四个世纪以前,足以填补中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方面的空白。”[11][p.188]
王士性对地理学的贡献,前辈学者皆有中肯评价,本文试就他对明代中后期云南社会生活与自然事象的考究为立足点加以评述。
三、王士性对滇云史地的考究
王士性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1590——1592)曾以按察司副使兵备云南澜沧卫(今永胜县),“余官澜沧两年”,[12][p.386]云南成为他在西南地区停留最久的省份,也是他志在游历的最后一站,“计了滇云,遂息足焉。”他载誉天下的《五岳游草》正是在滇期间结集,《自序》题款“时万历尝十有九稔,记者滇西隐吏天台王士性恒叔也。”[13][p.30]此后晚年“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有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14][p.238]在《五岳游草》的基础上提炼集为其地理学思想之大成的《广志绎》。这是一部采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泛论全国各地的地理差别,与传统地理志完全不同的一种通论式地理著述。
详检王士性相关著述,《广志绎》载云南史地最详(1~4卷均有提及),卷五尤有云南的专门记载,顾炎武的《肇域志》(参见续修四库全书本)几乎全文照录,仅加以批注(如关于审理江西抚州商贾案),并采用《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的标题冠名。
《广志绎》卷五云南篇资料来源由三部分组成,主要是作者的所见所闻,以及转录李月山《丛谈》和陈全之《蓬窗日录》的部分内容。
王士性引用李月山的资料,均注明“月山”字样,并在正文中两次提及“李月山谓”,“李月山备兵于滇,亲见之。”今考李月山者李文凤,字廷仪,广西宜山县(今广西宜州市)人,嘉靖乙酉(1525年)解元,壬辰(1532年)进士,由大理评事升广东兵备佥事,计擒海贼有功,“累官云南佥事,以疾归。”他“泛览博识书传之外,更勤咨访,从官京师及乘传所至,载笔自随,一有所得欣然录记,归乃辑次成书,曰《月山丛谈》。”另著有《粤峤书》二十卷。[15]据《千顷堂书目》,“《李月山丛谈》四卷,临海王士性删定”。[16][卷五;卷九八]《月山丛谈》的校勘者正是王士性,《月山丛谈序》记有王士性将该书辑佚付梓的经过。“初,是书出于邑人前参后军事屠君家,惜轶其第一、二卷,今年(万历十七年,1589年)夏临海王公以分藩右江至,偶语及此,公取视之,乃檄宜山使求全书,书得,亲为校勘。已,乃授工刊之治所,其冬过始安(今广西桂林市),属张子序”[17][卷五二]云云。今书未见。李文凤曾为官云南按察使佥事,从王士性辑刊《月山丛谈》,并在《广志绎》中频频标注转引,足见王士性对他的赏识与认同。
王士性摘录《蓬窗日录》时未提著者,只说“某《蓬窗日录》最长。”该书今有上海书店单行本(1985年版)两册,著者陈全之。据出版说明,此书所参版本是极为希见的嘉靖刊本。王士性节录的正是其中《寰宇》一门有关云南的几条材料。陈全之,字粹仲,闽人,嘉靖甲辰(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曾官山西参政,有《梦宣山人集》。[18][第四册]今云南学人史料笔记著录考证,陈全之“因故在滇期间与滇中诗人兰茂和兰廷瑞兄弟交往甚密。”他亲历过云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交通等,皆详细记录,悉心考订。故“该书为研究嘉靖时的云南提供了宝贵材料”。[19][p.20]今可与《广志绎》卷五云南部分互校。
由此,《广志绎》卷五云南部分的资料来源,均系明代亲历云南者所著述,史料比较可信。同时,王士性也以丰富而纪实的诗文,留下了他对滇云史地细心的考察和分析。[20][卷三二]
1.云南民间开矿与贸易用贝
王士性在滇期间,云南矿业有较大发展,开矿纳税已成为常例。他留意到云南各地民间私人采矿,分利合理,官民相安,自与别处不同。
“采矿事惟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劄而领煅之。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采矿若此,以补民间无名之需、荒政之备,未尝不善。”
在王士性这段为众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耳熟能详的文字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明初以来云南矿业开采、冶炼的生动场景。滇中民风淳朴,资源丰富,虽然民间自行组织开矿,其生产、冶炼、分配、管理都井井有条。组织者“硐头”;开采者“义夫”;监督者为官府有司,责任明确,秩序井然。尤其分配制度,类似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运作,产品按四份分利,即一部分上交官府课税,一部分留够硐头所谓的公私费用开支,余下就是硐头的收入和义夫的报酬,硐头具有的获利优势是显见的。此条材料还向我们展示了因采矿带动商业的发展,形成以开采地为核心集市的盛况。这是明末以前,云南采矿冶炼弥足珍贵的纪实资料,常常为论证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萌芽的学者所援引。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廷遣派中官到各地为矿监税使。宦官贪残,肆意搜括掠夺,一时流弊天下,怨声载道。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命内监杨荣开采云南”,遂有杨荣乱滇之事。杨荣矫旨滥采云南孟密宝井(在今缅甸境内,出产玉石),又要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荣由是怙宠益横,夷、汉居民恨入骨”。杨荣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境内各民族安宁的生活,最终激起群愤,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已卯“云南矿务太监杨荣被杀”。[21][卷六五]有明一代征收矿税的问题,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朝廷调遣中官干涉云南地方矿务的自行管理可见一斑。
王士性还记录了明代云南民间贸易用贝的事实。“贸易用贝,俗谓贝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盖八十贝也。”据《滇中琐记》,“至万历四年(1576年),以巡按御史言,开局鼓铸,而民间用尨(贝币的称谓)如故,钱竟不行,遂以铸成之钱运贵州充饷,停罢铸局,时万历八年(1580年)也。自此终明之世俱用尨。”[22][卷十一]
2.中缅边境地理状况及战事
王士性兵备澜沧卫期间,对中缅边境史地和中缅冲突颇为留意,有过深入的探讨。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夏,缅兵入侵,朝野震动,云南西陲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王士性凭着地理学家的敏锐,分析缅兵扰境将给内地带来调兵、转饷两大困难:
首先,王士性观察到缅兵每次进犯,总是有意选择酷暑时节,这样我方将面临非常不利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滇中兵每出则于蛮哈(驻今云南盈江县西布岭山铜壁关),其地在蛮哈山(在今铜壁关前)下,江(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恩梅开江)之北岸。最毒热多蝇,人右手以匕食,则左手乱挥蝇,稍缓,则随饭入喉中。”“内地兵一万,至其地者常热死其半。”中缅滇西边境明代设置南甸、干崖和陇川三宣抚司,高黎贡山的余脉,纵横其间,大金沙江、怒江切峡谷而下,高山深谷的地势常常使得朝廷的意图不能顺利到达这里。河谷低地带高温酷热的气候成为这一地区的特色。然而,缅方此举正是针对我方兵员多征自内地,不敌暑热的劣势。他留意到当地居民对付这样的高温,也往往剃光头发,整日泡在江水里以避暑,内地兵如何经受得了?所以当时惯用的方式,即调兵前要拨给被征调者所谓“买金钱”,事先让士兵安排好身后事,正反映了兵源朝不保夕的惨淡经营。加之军队供给费用庞大,“故调兵一个,其邑费银一万。”为凑足兵员,自然不考虑士兵是否具备作战的能力,可以想见其暗淡的战事前景。边境经年的争端与冲突,致使调兵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和麻烦,难怪王士性会称之为“一难也”。
其次,中缅边境遥在云南西部,地势险阻,我方劳师远征,战线过长,转饷是调兵之后必将面临的困难。王士性分析,“永昌(今保山市)至蛮哈半月,省城(今昆明市)左右至永昌又半月。”以永昌为中转站,仅运粮一事就会消耗一月的时间。加之“山阪险峻,运米一石,费脚价八金,仅一兵三月粮耳。”滇兵之调每以数万计,战争的旷日持久,大量兵粮及运费的支付,恐怕又在调兵“买金钱”的用度之上,因而“转饷之难,二难也。”滇西交通的艰难与险阻,王士性有切身的体验:“风尘莽白日,奔走无欢颜。青山抹马首,步步皆重关。石滑驱车苦,磴悬留足艰。巨坂欲造天,得往良畏还。又惧堕丛箐,冥行披草菅。路逢三两人,衣服尽斑斓。瘴疠眇天末,虎豹杂人间。”[23][p.205]凡此种种,上自按抚要员,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视用兵为畏途。然而,也有官吏混水摸鱼,趁机谋利,虚报缅兵人数以饱私囊,“盖永(昌)以外将帅偏裨,无不乐用兵以渔猎其间者。故缅至,每每作虚报。”据王士性实录,这次辛卯(1591年)夏之战,“余闻缅二千人渡江,而参戎报二十万也。”[24][卷五]
基于上述我方作战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考虑,王士性认为每次迎战朝野骚动,劳民伤财,不是长久之策。于是,他提出一套坚壁清野,转嫁调兵、转饷之难于缅方的建议,即自金沙江(今缅甸境内恩梅开江)以东,明朝所辖三宣夷寨全部迁至内地,“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则彼既不得因粮于敌,若转饷而至,其受累与我同,缅夷盗劫之辈庶其阻江而止乎?”以大金沙江为天堑,弃土地以换安宁,他认为是可行的。他还佐以例证,“大宁神京拥护,哈密屡世属夷,本朝业已弃之,无非权其利害之重轻,于云南万里外千里荒服之地,何有不然?”否则,“滇人终无息肩之期矣。”王士性所指明朝放弃的大宁,即北直隶境内的大宁都司,初治内蒙古宁城西,永乐后迁治今保定市;西北方面,明初势力最远到达新疆东部的哈密和青海柴达木盆地,曾设置哈密等五卫。15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屡遭瓦剌、吐蕃的侵扰,嘉靖八年(1529)明朝放弃了这些地区,退守嘉峪关。[25][p.116,148]
从王士性的上述分析中,其地理学家审时度势的态度是不难发现的,至于他的建议方案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作为边官,其职责的重要方面应该是守土靖边,保境自固,岂可置千里之地于不顾,以土资人!此论不可行!尤不可乱比附。中缅边事,有其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非本文所能说清。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的发展事实确如王士性所言,此方大片领土已为缅境内一些独立部落所占,今已不在界内。但寸土不可丢,是为政者们必须谨记的。
3.对自然地理事象及其规律的考究
王士性在滇短短的两年时间,他的著述中记载了较丰富的明代云南政治疆域、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状况,以及各地少数民族习俗和节庆等。如云南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有三种来由:一说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一说孟获被诸葛亮擒纵得归,一说梁王擒杀段功之日,群众举火把为纪念英雄人物和祭祀、祈祷消除灾祸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将这三个与历史事件相关的传说演绎成火把节的来历,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对勇敢、正义、智慧、和平的崇尚和向往。
王士性也留下了有关云南山川、湖泊、气候、地形等方面的精辟见解。
例如,滇池一带的气候“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长,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他认为其成因在于云南地处高原,靠近西北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气温随地势增高而降低,故偏寒,又位于低纬度地带,加之地势极高,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故不冷不热,冬夏季节昼夜变化不大。指出这还与云南地区多湖泊,可调节湿润度,同时盛行西南季风等不无关系。这一见解可以说已具有现代科学的眼光。“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迩,地势极高,高则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镇日皆西南风,……地多海子(湖泊),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
他还从宏观的视角对云南山脉水系的北南走向,万壑深涧,又东西同纬度区域气候相似的春秋景象作了描绘。“滇中长川有至百十余里者,纯是行龙,不甚盘结,”地形北高南低,河流一泻千里,“行东西路上,不热不寒,四时有花,俱是春秋景象。”寥寥数语,滇云地形地貌和气候四季如春秋的景象就已显现在我们眼前。
王士性任职按察副使,兵备澜沧卫,驻大理府(治今大理市),政务之余不忘游历滇西山水,著有优美的鸡足山、点苍山、九鼎山游记及配图存世。他对大理情有独钟,“余游行海内遍矣,惟醉心于是,”他总结说:“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他还进而表达了“欲作莬裘,弃人间而居之”的心愿。
王士性就曾数次流连于苍洱之间。他在《游点苍山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名称、方位,以及洱海三岛、四洲、九曲等的具体称谓。尤为可贵的是,他为我们描绘了“点苍四景”,即“溪甸晴雨”、“鸳浦夕阳”、“晓峡月珠”和“夏山云带”,并对四景的命名内涵作了解说。“溪甸晴雨”——“溪甸十步,此雨彼晴,雨喜栽禾,晴欢刈麦”;“鸳浦夕阳”——“马龙峰缺,返照一线,投光而浴,时见双鸳”;所谓“晓峡月珠”,其内涵是:“下关之峡,有月出水,山月已沉,水月故在”;而“夏山云带”则是“夏秋白云,山腰一抹,不流不卷,树梢出没。”[26]
他分析以上四景的成因,实在是“兹山晦明,变态之巧”,即季节、昼夜变化,自然景观和气象随之改变的反映。四景的生动描绘,不啻于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苍洱间美不胜收的图画。如“溪甸晴雨”一景,主要出现在四五月间,天气忽晴忽雨,苍山的溪畔田野,人们雨则栽种秧苗,晴则收割麦子,可体验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默契。又如“夏山云带”,今又称“云横玉带”,即苍山“玉带云”,现于夏秋季节,预兆丰年,与望夫云一起为苍洱两大云景。可供今天从事气候物象之观赏与科考。
王士性还对安宁温泉旁的“圣水三潮”景观发生过极大的兴趣。“余过安宁,问所谓‘圣水三潮’者,觅之,乃在温泉之傍,大树之下。一穴如斗,每日申、子、辰三时水自溢出,余时则干。”他考究其成因,“此自造化诡幻灵气使然,难以常理论。”[27][p.246]他还以此为例驳斥海潮现象是与“海鳅”有规律的出入相关的谬论,“鳅游何以时刻必信如此?矧鳅寿有限,安能与天地相持?是一鳅耶?众鳅耶?”
关于海潮的成因,他探讨了唐代卢肇的“从日说”,元代邱处机的“因月说”和宋人苏子瞻的“随星说”,逐一辨析,指出三人的结论不过是按常理推测,并没有找到一种合理的解说,“是三君子之言皆以理测,而不知天地造化有不可专测以理者。”虽然王士性的解释陷入不可知论,但他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却是可取的。徐霞客也曾游历到此,在他的游记中,三潮奇观的形成是因金酋黾(蟾蜍的一种)有规律的出入所致,[28][p.843]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不免落入“海鳅”一类的窠臼。其实,三潮景观并不神秘,它是自然界的一种潮汐现象。由于这里地下的积水空间有限,出口狭小,加之大气压力等作用,一旦蓄满水,多余的水就会从出口处涌出。当水排到一定的程度,泉涌的情况就会消失,类似潮水有规律的涨落。这样就出现了三潮的景观。当然,圣水三潮的形成还与泉的水量恰巧在一天三个不同的时间,及时补给,按时喷涌,有密切的联系。王士性对潮汐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显然较徐霞客更为深入,也更接近客观实际。
另外,王士性在云南曾以滴漏作过检测时差的实验,之后又据钦天监月食记录验证。“李月山谓,滇中夏日不甚长。余以漏准之,果短二刻。今以月食验之,良然。”[29]他采用的实验方法已明显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对云南夏季时差的描述准确。
当然,作为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记录与考察也并非尽善尽美,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士性在记载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中,转录了李月山记载的“地羊鬼”能易人心肝之术等无稽之谈,以讹传讹,不足取。
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开篇一言:“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这里王士性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他说“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而滇、贵设郡县实启自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大概因为西南地区素为中央羁縻之地,王士性或许特指从明代开始推行“改土设流”,才正式将西南地区纳入制同内地的管理体系。[30][p.366-369]不然,作为一个擅长人文地理的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当地的沿革建制。此言自有王士性所受的时代局限。
综合王士性著述中关于云南史地的记载,笔者认为,由于王士性在滇任官达两年,且细心观察和考订所到之处的社会人文和自然地理事象,他的绝大多数记载是可信的,有不少见解甚至是科学的超前的,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云南明代史地资料。其中,他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如安宁温泉与“圣水三潮”的考究,“点苍四景”涵义的阐释,火把节的三种来历等,对今天云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颇多借鉴。
四、余论
“王士性研究”发轫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迄今已近二十年。目前浙江学者的研究已成果累累,而云南方面对王士性的关注还不够。因此,作为当年徐霞客成就最大的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学人关注徐霞客与王士性的比较研究,无疑将不断丰富和深化这一课题,这对建设云南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也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同时,徐王比较研究旨在从对比中发掘他们对地理学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不是要分出二人的高下,可以说二人的贡献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地理学界一度出现过的“抑王扬徐”,和近年来为突出王士性成就的“抑徐扬王”倾向,均是对二位地理学家不公正、不客观的态度。如何确立一套合理评价地理学家贡献和地位的价值体系,恐怕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无论于徐、王二人贡献的正确认识,抑或评价古往今来的众多地理学者的成就,甚或完备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长水集·续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徐建春.从重视徐霞客到重视王士性:中国人文科学复兴的一个标志[J].浙江社会科学,1994,(2).
[3] 杨文衡.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王士性[J].徐霞客研究第2辑,1998,p.153-155;冯岁平.徐霞客游记记述的王士性[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p.213-217;魏子云(台湾).徐霞客笔下的王十岳[J].徐霞客研究第4辑,1999,(1):p.124-128.
[4] 朱惠荣.徐霞客与云南[J].云南社会科学,1994,(6).
[5] 李惠铨.(明)王士性〈广志绎〉初刻年代辨正[J].昆明市志办《史与志》,2002,(4):p.45-46;李寿,朱端强等.云南史料笔记随录一[J].广志绎附五岳游草[J].载昆明市志办《史与志》,2001,(1).p.22-23.
[6] 台州府志·王士性传(卷十),康熙六十一年刊本[M],转引自《广志绎》1981年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本[M].另参见《王士性行迹简表》,载《王士性论稿》[M].;又《王士性行迹系年长编》,载《王士性地理书三种》附录[M].p.668-684.
[7] 广志绎·杨体元序.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9] 王士性.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徐建春.王士性及其广志绎[J].杭州大学学报,1990,(3);徐建春.王士性研究三题[J].浙江学刊,1994,(4);周振鹤.王士性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J].东南文化总102期,“王士性研究专题”.
[11] 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2]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 五岳游草·自序,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 广志绎·自序,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七十)李文凤传[M].四库全书本;另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六四《庆远府·李文凤传》[M].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天启《滇志》卷十二《官师志·佥事》[M].《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M].《粤峤书》见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题为《越峤书》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钞本)[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蓝格钞本.
[16]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M].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九八《艺文志三》记“李文凤《月山丛谈》十卷”[M].
[17]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五二)[M].张鸣凤.月山丛谈序[M].
[18] 陈田辑撰.明诗纪事(第四册)卷八己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9] 段润秀,杨林.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J].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2,(1).
[20] 天启《滇志·搜遗志》卷三二:“崇阳汪文盛,四明张时彻,白门刘麟,长州皇甫,番禺郭,天台王士性,吴郡冯时可,皆著声文苑而官滇,著作尤多。”古永继校点本[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21] 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2] (清)杨琼.滇中琐记·贝.引自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3] 五岳游草·滇粤游下(卷十)行定西岭即事,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4]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云南[M].记此事始末,有云:“丁苴、白改盗山箐在临安、南安、新化之间,乃百年逋寇,辛卯(1591)夏因缅报调兵,后缅退而兵无所用,吴中丞遂檄邓参戎子龙移师袭之。……遂悉荡平之。人谓吴好用兵邀功,然此举良为得策。”案:(清)鄂尔泰、尹继善修,靖道谟纂《云南通志》卷十六下《师旅考》,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有记此事:“万历十九年(1591)(莽)应里围蛮莫,邓子龙率兵至卜罗思庄,缅退去。丁苴、白改夷普应春等叛,抚镇吴定、沐昌祚讨平之。”据天启《滇志》卷二《地理志》,丁苴、白改平乱之后,在当地平甸乡设置新平县。此处参戎当指邓子龙,王士性还记与之共商打击五井盗盐贼事宜.
[25]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26] 五岳游草·游点苍山记.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p.146;又参考喻学才.王士性与白鸥庄[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p.84.
[27] 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8] 徐霞客在文中记:“党生言,穴中时有二蟾蜍出入,兹未潮,故不之见,即碑所云‘金酋黾’,号曰’神泉’者矣。”校注:“《寰宇通志》云南府井泉:‘海眼泉,在安宁州治北,每日三潮,随涌随涸,世传戒照禅师卓锡所穿之泉。’被围存。”见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29] 关于这次月食时间,据《广志绎》(中华书局本1981年版)、《肇域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及《广志绎》(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均载“万历二十年五月十六望,月食,据钦天监,行在乙亥夜,月食八分一十九秒……”;读《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却记“万历二十五年,月食,……”,p.383;《附录》“万历二十(壬辰)年,四十六岁。五月十六望,日食,在云南救护月生光一半以上,不及三分而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误将二十年刻为二十五年,月食刻为日食,是为校勘不慎,今指正。
[30] 覃影.浅析王士性眼中的西南“改土设流”之弊端,李鲜,杨建昆.西部科研文荟[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覃 影(1974—),女,四川兴文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与文化资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