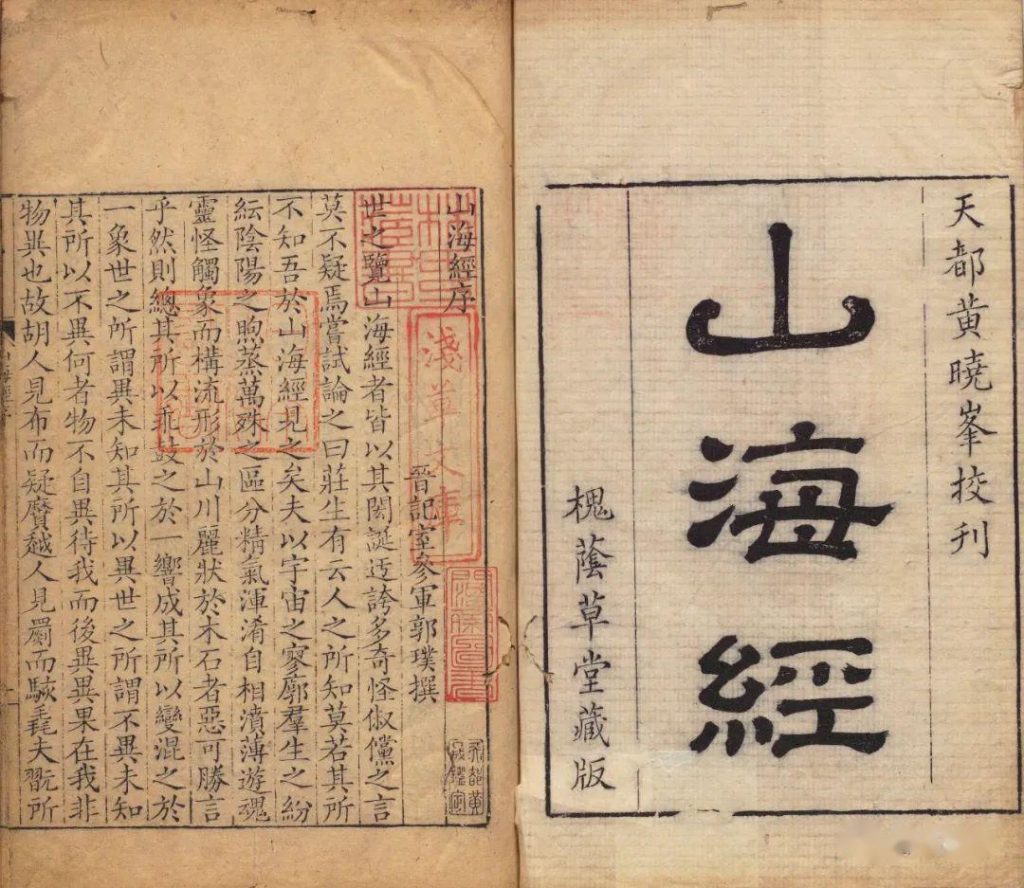
《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全书虽不到三万一千字,但它却记载了约四十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以及这些邦国、山、水道的地理关系、风土民俗和重要物产。此外,它还记载了百多个历史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世系或活动。无疑的,这些记载是研究我国以及东亚、中亚各族人民上古时代的生活斗争、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它所记载的东西有很多不为后世读者所理解,而常被斥为“恢怪不经”。著名的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曾一叹它“放哉!”再叹它“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后世以“怪诞”指斥之者,更是屈指难数。有的人甚至把它排于“史部”之外,如清代所纂的《四库全书》,就把它从地理类改放到小说家类中;并说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以后,此书才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后来的古史学者,也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片段地征引;而对该书仍指斥为“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系亦以子虚乌有视之”。都没有对该书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考察,还不能把该书提到古史研究的恰当的地位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在考察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就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内容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真相。因此,作者在这里愿就《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和地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同志们讨论。
一
《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说法不同。中原文化传统可以魏国的《竹书纪年》、赵国的《世本》以及后来《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的《五帝本纪》等作为代表。这些文献记载,都是起自黄帝,而且是以黄帝作为传说的中心,把后世帝王都列为黄帝的后代。《山海经》则不然,它虽曾十次提到黄帝,但它却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提到帝俊者有十六条,提到帝颛顼者有十七条。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帝颛顼的后代。特别是帝俊,他在《山海经》中的地位,俨然有如黄帝在中原传统中的地位。他不仅被当作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季厘之国、西周之国的始祖,而且把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后稷,也认为是帝俊所生(《大荒西经》)。而中原传统说法则以后稷是黄帝的后裔(《世本》《周本纪》)。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创造发明者的传说上,《山海经》所记不仅与《世本》不合,并且《山海经》也是以帝俊为中心,而《世本》则以黄帝为中心。我们把两书的数据作过一个对比表:
不难看出,《山海经》所载竟没有一项和《世本》相合;虽后稷播百谷一项与《孟子》同,却又不见于《世本》。同时,据《大荒西经》所载,虽然说稷“降以百谷”,但又说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故又尊叔均为“田祖”。实际上是以叔均为农耕之祖,而叔均则不见于中原的传说,故两者在实质上仍然不同。又据《山海经》的记载,它所载的发明者如番禺、吉光、晏龙、义均、后稷、叔均等都是帝俊的子孙。而《世本》所载的发明者如鼓共、货狄、牟夷、挥、胲、奚仲、鲧等,据《世本》注家宋衷等的解释,他们都是黄帝的臣子或子孙。《山海经》以帝俊为中心,《世本》以黄帝为中心,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山海经》中这样重要的帝俊,却不见于先秦的中原传统中。王国维曾根据晚在魏晋时期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说法,认为帝俊就是黄帝的玄孙帝喾。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山海经》中同一篇内为何既有帝俊又有帝喾(如《大荒南经》)。而且如以中原传说的其他世系关系来理解帝俊,则将发生更大的混乱。章太炎曾说过:
帝俊生中容,高阳也;帝俊生帝鸿,则少典也;帝俊生黑齿,姜姓,则神农也;帝俊妻娥皇,则虞舜也;帝俊生季厘、后稷,则高辛也。(《检论·尊史》)
帝俊自帝俊,帝喾自帝喾;《世本》自《世本》,《山海经》自《山海经》,本来各是一个系统,强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全,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山海经》虽多次提到黄帝,也多次提到轩辕,但从未认为黄帝与轩辕是一人。这与其他古代南方作品的看法是一致的。《越绝书·记宝剑》载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庄子·胠箧》也以轩辕、赫胥的时代早于祝融、伏羲、神农。都是不以轩辕、黄帝为一人,而且轩辕早于黄帝甚远。同时,《山海经》所载的轩辕之国也不在西北而在西南。《大荒西经》说:“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海外西经》又说:“辕轩之国,在穷山之际。”郭注:“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岷山之南。’”郝懿行《笺疏》谓江山即岷山。巫咸、女子、轩辕三国相接,《笺疏》说江山即岷山,允当。也可能郭氏所见《大荒经》本作岷山,后来传本始作江山。即以原作江山而论,古代北方但言河,江称绝不用于西北。若江山为岷山,即《山海经》之崌山,岷山所出之江水为青衣江(详后),则轩辕之国岂不位于青衣河谷?《山海经》的这些看法,和《五帝德》《帝系姓》以及《世本》《史记》中关于轩辕、黄帝的说法是迥不相同的。
《山海经》关于帝颛顼的记载中,虽也谈到颛顼和黄帝有着世系关系,但它却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海内经》)。这和《世本》所载“昌意生颛顼”的说法便相差一代。它在另一处又说:“少昊孺帝颛顼。”(《大荒东经》)如依《说文》所说“孺,乳子也”,则昌意、颛顼之间便不仅是差不差一代的问题,而是他究竟是不是昌意的后代的问题了。同时,中原传说只载颛顼是舜、禹及老童的先世,而《山海经》所载,除颛顼生老童一点与中原传说相合外,还载了他是季禺、鼬姓、淑士、叔歜、中䡢、驩头等国的始祖。其地位显然比中原传说中的地位重要多了。
至于中原传说中所载黄帝的子孙帝喾、帝尧、帝舜等人,《山海经》中虽也都曾提到,但却看不出他们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不仅看不出他们和黄帝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并举帝喾、帝尧时,总是把帝尧列在帝喾的前面(见《海外南经》《海内北经》《大荒南经》),似乎帝尧还在帝喾之先了。无疑的,这又和中原传统是相悖谬的。《山海经》也曾多次提到禹和鲧,但它所载的世系也和《世本》大不相同。《世本》说:“颛顼生鲧,鲧生禹。”而《山海经》却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海内经》)虽然两书还同认为他是黄帝的后裔,但其世系则各殊了。又如《山海经》说“舜死苍梧,葬九嶷”(《海内南经》《海内经》),而《孟子》却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一直没有超出东方的范围。一南一东,也大相径庭。后世注家或说鸣条在南,或说苍梧在东,都只不过是不顾地理的确定性而强合二系之传说罢了。
羿,或称夷羿,也是一位南北都共有的传说人物。但是,在评价上则南北颇有距离。《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外南经》又说:“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杀凿齿事在《淮南子·本经》中有较详的记载,它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㺄、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㺄,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当正因此,所以《泛论》又说:“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高诱注:“祭田为宗布。”大概羿死后当上了田神。《淮南子》所载羿的这些活动,当正是《海内经》所说的“以扶下国”“去恤下地之百艰”的具体内容。《海内西经》称之为“仁羿”,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淮南子》也是南方的作品,所以它和《山海经》能基本一致而又相互补充。而在北方传说中的夷羿,却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了。《左传》襄公四年说: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传》又载《虞人之箴》说:“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这就完全是一位只知射猎佚乐的昏君。《论语·宪问》也说羿“不得其死然”,显然是一种指斥。至于《离骚》《天问》中的羿,则又似以南说为基础而综合南北两说的产物,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述分析,说明了《山海经》和《世本》不论在人物世系上或事物的创造发明上,两书都各有一套互不相同的说法。但是,《世本》的说法虽不同于《山海经》,却和《竹书纪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等书的说法相合。这些作品都是产生于中原地区,是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山海经》是另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一个文化传统。
其次,我们从记叙四方方名的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山海经》和中原传统的不同。先秦中原文献在四方方名同时并举时,其排列的顺序一般都是以东、南、西、北为序,如《尚书·尧典》在命羲和敬授民时以四方配四时是“……平秩东作……平秩南讹……平秩西成……平秩朔易……”在叙舜巡四方时,其顺序是“岁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也是以东、南、西、北为序。其他如《墨子·贵义篇》《管子》的《五行》《四时》等篇,也莫不以东、南、西、北为序。这种排列顺序在甲骨文中也同样存在(见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可见这一排列顺序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但是,《山海经》中的排列顺序则与此迥不相同。今《山海经》十八篇,共可分为四组:《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各组都各有东、南、西、北四篇(《五藏山经》另有“中”一篇),而其排列的顺序则是南、西、北、东。如《五藏山经》五篇,其次序是《南山经》第一,《西山经》第二,《北山经》第三,《东山经》第四,《中山经》第五。《海外经》四篇的次序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从篇中内容看,也是由西南而东南、而东北,再由西南而西北、而东北。《史记·天官书》载有“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之说,也正是由西南而西北、而东北(唯《东山经》是由东北而东南,为大同而小异)。《海内经》四篇的次序也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篇内叙述是始于东南而西南,而西北,亦终于东南,也和前两部分的叙述内容大抵相同。只《大荒经》部分稍异,它的排列顺序与《尚书》《周礼》《墨子》等书相同,是以东、南、西、北为序。据郭璞说,这五篇(包括《海内经》一篇)本在献书时所进十三篇之外,毕沅认为是刘秀时所附。我同意这个说法。在汉代校书之时,很多古籍都曾加以编订,已不是本来面目。考《淮南子·地形》所记海外三十六国,与《大荒经》所记大抵相同,应当是《淮南子》取材于《山海经》。《淮南》叙三十六国的顺序是自西北开始,而西南、而东北,和它叙九州、叙八殥、八纮、八极的方位顺序都不同。《淮南》本是杂取各书,互不相同,当正是保存了各书的原有面貌。因此,可以认为《大荒经》原本的顺序是自西北而西南、而东南、而东北,其四篇的次序当是以《西经》开始、而以西、南、东、北为序。这个排列顺序虽和前三部分有所不同,但它和中原传统的以东、南、西、北为序的差异,仍然是很显著的。四方方名排列顺序的不同,虽然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但它却同时是文化传统不同的一个反映。
古代长江经有九江一地,而南北之说各异。《中山经》说:“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据此,九江显当在荆州洞庭。《水经》卷40说:“九江地在长沙下嶲县西北。”《路史余论·九江详证》引张勃《吴录》说:“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蔡沈《书集传》引《楚地记》说:“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下嶲、巴陵在汉长沙郡,属荆州。三说皆与《中山经》合,这是南系的说法。《禹贡》说:“九江孔殷。”又说:“过九江,至于东陵。”《汉书·地理志》说:“寻阳,《禹贡》九江在南。”“金兰西北有东陵乡。”寻阳、金兰皆在庐江郡,属扬州。此《禹贡》九江显当在扬州庐江。《史记·河渠书》说:“余南登庐山,观禹所疏九江。”也认为《禹贡》九江在庐山。这都是北系的说法。南北说法本自不同,后世注家常常不加分辨,以致造成混乱。如郭璞以《汉志》释《山海经》,而蔡沈、魏源又以《水经》释《禹贡》,其误维均。《水经注》保存了不少古说,这是很足珍贵的,但它也常常用南说来理解《禹贡》山水泽地,仍多未当。
吕子方先生曾根据《海外东经》所载“五亿十万九千几百步”的记载,指出《山海经》是以十万为亿,和中原传统以万万为亿者在计数方法上不同(将另有专文)。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毫无疑问,计数方法的不同,也同样是文化传统不同的一个反映。
二
如上所述,《山海经》既不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那么它是什么地区的产物呢?这便是我们准备在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作者在三十多年前曾写过一本《古史甄微》,探讨中国古史传说的问题,认为上古居民约可划分为三个集团,分布在北(河洛)、东(海岱)、南(江汉)三个地域。先秦的学术文化也大体可划分为北(三晋)、东(齐鲁)、南(楚)三个系统。对于古史的传说,也由于文化系统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当时曾以《韩非子》《竹书纪年》所记古史作为北系的代表,以儒、墨、六经所传古史作为东系的代表,而以《庄子》和《楚辞·天问篇》所传古史作南系的代表。当时也曾因《山海经》的记载多与《庄子》和《天问》相合而认为它是南系作品之一,曾写过一篇《天问本事》,就是专以《山海经》证《天问》。但在当时,还只因《庄子》《楚辞》二书同是楚国的产物,而定其为南系,还没有从《山海经》本书以探求其为南系的作品。现在拟专就这点提出一些意见。至于《山海经》与《庄子》《天问》在古史传说上的共同之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没有发明使用经纬度记载一定地区的地理位置的方法之前,一般都是用东、南、西、北等方位词来记载。但这种记载方法对一定具体地区说来,都只能是相对的,是随着观察者所采用的基准点而有所不同的。如以整个亚洲为基准,则小亚细亚等地区为西方,一般称为西亚;而以欧洲为基准,则小亚细亚地区为东方,是“近东”一词所由生。又如以北京为基准,则河南省为南方;而以武汉为基准,则河南省便是北方了。古文献中所记载的方位,其情况也正如此,是随着文献所代表的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如中原文化系统的文献所说的“中”,便是指的中原地区。《史记》载范雎说:“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范蠡说:“陶为天下之中。”而《山海经》则不然,它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从《五藏山经》五篇——《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来看,《中山经》所载的地区,无疑的当是这部分作品所认为的“天下之中”。《中山经》所记载的是哪些具体地区呢?
《中山经》篇中共分成十二段来叙述,称为“十二经”。前七经所载各水道,都是注入河、洛、伊、谷等水,都在古豫州西部地区。《中次八经》所载各水道,都是注入江、漳、睢等水,这三条水道都是在古荆州西部。《中次九经》中所载各水道都是在岷山山脉地区,东注入江(今岷江),说明《中次九经》所载之地为今四川西部,为古梁州西部。《中次十经》无水道,有首阳山及涿山,首阳即鸟鼠,涿山即蜀山(从郝懿行《笺疏》说),则所载当是古梁州西北地区。《中次十一经》载有湍、潕澧、沦等水道,多是注入汉水或汝水,都在古荆州地区。《中次十二经》载有洞庭之山,有澧、沅、潇、湘和九江,都在古荆州南部。根据《中山经》这些记载来看,《五藏山经》所谓的“中”无疑的是包括了古豫、荆二州的西部、南部和整个古梁州地区。这和中原地区以韩、魏为天下之中是迥不相同的。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不仅《中山经》把巴、蜀包括在“天下之中”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同时它对岷江中上游地区的水道情况的记载更是值得注意的。记载这个地区的是《中次九经》,其中关于水道的记载是:
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五百里曰鬲山……蒲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茈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
所记八条水道,除后四条外,都还可以察考。洛水即今流经什邡之洛水;出岷山之江水,即今岷江;出崃山之江水,即今雅安地区之邛水;崌山的“崌”字当为“岷”字之讹(岷字汉常作崏,易讹为崌),就是蒙山,出崌山的江水就是出岷山西的沫水。这四条水道,除岷江而外,都是不大的水道。其余四条不可考的东注于岷江的水道,也当是小水,所以不可考了。据《山海经》的体例,同在一经者其地理位置相近。则这八条水道都当相去不远,可能都在岷江流域,甚至还可能都在岷江中、上游,在今乐山以北。我们知道,《山海经》所记的地理区域很广,远远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围,很多地方甚至还超出了祖国现在的版图。对各地区的记载,都只能很简单。但对这块方圆不过几百里的岷江中上游地区竟记载了八水十六山,相对说来,应说是很详细了。根据古人著书详近略远的惯例(特别是地理知识的记载更是如此),则《五藏山经》不仅是以巴、蜀、荆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其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海内经》四篇所说“天下之中”的地域。《海内经》只有《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而无《海内中经》,则《海内经》这部分所说的“中”只能从《东经》之西和《西经》之东来间接推求。考《海内东经》记载了江水、濛水、白水,即今之岷江、大渡水、白水河,都在四川西部。应当说,它所说的“中”也当在四川地区。《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高万仞。”郭璞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此自别有小昆仑也(上八字据《水经注》补)。自此以上二千五百余里,上有醴泉、华池,去嵩高五万里,盖天下之中也。见《禹本纪》。”《山海经》《禹本纪》被司马迁认为是内容相近的两书,郭璞引《禹本纪》来解《山海经》,应当说是正确的。在这一前提下,则《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便当是这个“海内昆仑”了。这个海内昆仑在什么地方呢?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因此,我们认为《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是指今四川西部地区。
现在,再来看看《大荒经》以下五篇所说的“天下之中”。今本《大荒经》共四篇——《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这四篇后面有一篇《海内经》,是《山海经》最后的一篇。从《山海经》全书篇目体例来看,这一篇与他篇颇不相类,它应当是《大荒经》的一部分。《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海内经》文句,就称之为《大荒经》,可见晋、宋间人所看到的传本都还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把这五篇合在一起来考察。《海内经》说:“西南黑水、青山(二字从裴骃《集解》补)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注:“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郭注二语也见于王逸《楚辞·九歌》章句。但王逸称之为《山海经》。则此二语当原是经文,后被传写误入注中。都广即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属成都市〖《海内经》说:“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此作“广都之野”。《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郭璞注:“在广都之野。”说明“都广”又或作“广都”。《淮南·地形》言“建木在都广”。张衡《思玄赋》“躔建木于广都”,显即据《淮南》,但《淮南》各种传本无作“广都”者。但李贤、李善注《思玄赋》所引《淮南》却同作“广都”。不知究系古本《山海经》《淮南子》本作“广都”,抑或后世所改。此等差异当是传本不同,可不必辨其谁为正者。《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本治广都樊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知蜀开明王朝曾建都于此,汉武帝元朔二年置广都县于此,唐、宋以后改为双流县。〗。都广既是“天下之中”,正说明《大荒经》以下五篇也是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同时,《大荒海内经》共记载了十六个国,其在北方、东方只有六国,其余十国都在西南方,同样是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当也正说明其属西南文化系统。
《海外经》四篇所载之地,皆在《五藏山经》所记之地的四周,其山水国物又多有与《海内》《大荒》等九篇重复者,而独不与《五藏山经》重复,可知《海外经》与《五藏山经》当是一个著作的两部分。而且《海外经》所载又都是遥远地区,无助于“天下之中”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就只好从略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可知《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
从前,有人曾就《山海经》所载的生物进行分析,发现它所记载的亚热带、热带的产物较其他先秦古籍为多,从而认为山海经是印度人的作品〖卫聚贤说,见所著《古史研究》第二集〗。说《山海经》是印度人的作品,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但他所作生物产地的分析,却正是《山海经》是南方文化系统的作品的有力证明。因为古代中国南方气候远较现在炎热,《山海经》所记载热带、亚热带的生物,正是古代中国南方气候条件下的产物(关于古代中国气候问题,作者别有专论)。
我们不仅可从《山海经》所说“天下之中”以说明其为南方文化系统的作品,还可以从所说“天下之中”的具体地区,再对作品的产地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上面对“天下之中”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山海经》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虽然同在南方,而其具体地区则又各不相同。而且三个部分的记载又常有重复之处,甚至互有出入以至抵牾。这都说明:三个部分虽然同属南方系统,但又有南方不同地区的差异。
先看《海内经》部分。《海内东经》记了二十多条水道,但却不记黄河而记漳水于章武入海。章武正为黄河改道行漳水后的入海口。北人应知此时之漳水即是黄河,而此经但谓之漳水,知此经不作于北人之手。同时其对长江的记载也颇奇特,它讲了灌县以上岷江(当时认为即是长江)发源地区的三江,而不记长江入海地区的三江。发源地区的三江是小山小水,入海地区的三江是大江大水,这种详小略大、详西而略东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古人著书受到闻见的局限,多详近而略远。以此衡之,则此《海内经》部分必非吴越地区的作品,而当作于蜀中。
但是,关于岷江上游的山水,旧解颇多歧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主题而对这地区的小山小水进行一些探讨。《海内东经》说:“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入海在长州南。”既说大江、北江、南江是“岷三江首”,无疑这是岷江发源处的山水。《水经注》序南江(原讹作中江,从《水经注疏》正)、北江于汶江道上,正是把二水理解为岷江上源,这是正确的。但《水经注》在这里却用崌山、崃山来取代高山、曼山,这就是误读郭注了。考《中山经·中次九经》载:“崃山,江水出焉。”郭注:“邛来山,在今汉嘉严道县,南江水所自出也。”“崌山,江水出焉。”郭注:“北江。”但是,郭注此处所说的南江、北江,与上揭“岷三江首”的南、北江并不是一回事。虽同具南、北之名而其本名则异。《汉书·地理志》蜀郡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水经·青衣水注》也说:“(邛)水出汉嘉严道邛来山,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水经·江水注》又说:“崃山,邛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崃”“来”同是一字。这些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出于崃山的江水,应当就是邛水。《初学记》卷8引《山海经》此文作“峡山,邛水出焉”,很显然“峡”字是“崃”字之讹,“邛”字是“江”字之讹。但也可能是《初学记》作者正是用“邛水”来理解此处的“江水”,所以改“江”为“邛”。我们既从崃山找出了出于崃山的江水是邛水,同样也可从崌山来寻找出于崌山的江水是何水。但是,崌山一名仅见于《山海经》,自来没有人解释过这山在何处,这就给我们寻找这条水道带来困难。但《山海经》曾说崌山在崃山东一百五十里(《中山经》),崃山既在汉嘉严道县,则崌山当也在严道或严道附近。《水经·江水注》根据《山海经》载有崃山、崌山,它说“崃山在汉嘉严道县”,这是正确的;但它又把崃山、崌山都叙在蚕陵县之下汶江道之上,这就不正确了。汶江道为今茂汶羌族自治县,严道为今荥经,两地的距离远超过了一百五十里。把这二山叙在汶江道之上当然是错误的。我认为崌山的“崌”字当是“岷”字之讹,汉代“岷”字常作“㟭”,易讹为“崌”。这个岷山,应当就是蒙山。《水经·沫水注》说,岷山即蒙山。《续汉书·郡国志》说:“汉嘉,故青衣,有蒙山。”青衣在今雅安北,雅安、荥经之间的距离,略与《山海经》所载崃山、崌山之距离相合,因而以青衣之蒙山为《山海经》之崌(岷)山是完全合适的。崌(岷)山既已寻得,则出于崌山的江水也就不难推定了。《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蒙)山西,东流通汉嘉郡。”《水经》又说:沫水“东北与青衣水合,东入于江”。这就应当是《山海经》所说出崌(岷)山而注入江水的“江水”。旧说多以此沫水为今大渡河,这个说法不正确。《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华阳国志》曰:‘二水(青衣水、沫水)于汉嘉青衣县东为一川,自下亦谓之青衣水。’沫水又东径开刊县,故平乡也。”《水经·青衣水注》又说:“青衣水径平乡,谓之平乡江。”这里的青衣水就是上文所说二水合为一川的青衣水。从这两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青衣水的上源有二:一为沫水,一为青衣水,二水在青衣县汇合后,或称沫水,或称青衣水,在流经平乡后,又称平乡江。《水经》所说的青衣水,大家都承认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沫水既是青衣江的上源或汇合后的青衣水,当然就绝不是今之大渡河了。今之大渡河当为古之渽水。《水经·江水注》说:“(渽)水出徼外,径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因此渽水在唐以来遂有大渡之名。古之大渡水为今之青衣江(古青衣水即大渡水一事,只需就《汉志》青衣下班固自注、《水经·江水注》所说大渡水与《水经》青衣水对勘便很清楚,毋庸置辩)。渽水于南安入大渡水入江,即今大渡河在乐山与青衣江合再入岷江事。如以古沫水为今大渡河,则古之出自徼外的源远而流长的渽水岂不便化为乌有了?这是绝对不妥当的。因此我认为出崌(岷)山之江水是沫水,在今雅安地区。在明确了出崃山之江水为邛水,出崌山之江水为沫水后,而邛水正在沫水之南,对郭注之所以称出崃山者为南江、出崌山者为北江,便也容易理解了。显然,出于崃山、崌山的南江、北江是在汉嘉(今雅安地区),而出于高山、曼山的南江、北江则在汶江道(今阿坝州茂汶县)以上,两者是绝不应混淆的。刘昭《郡国志》注于汶江道下引《华阳国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这两条水出自汶江道,其位置在成都西,可能就是出于高山、曼山的南、北江,但这二水为今何水则已不可考,高山、曼山为今何山亦不可知。然此高山、曼山、南江、北江之为小山小水当是无可置疑的。《海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在《海内东经》还载“白水出蜀,东南注江”,这是《山海经》中唯一提到蜀的地方。此外,《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而其他部分却不见开明的记载,应当承认,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
再看《大荒经》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这也是《山海经》其余两部分所不见的。同时,《山海经》中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这部分(《大荒海内经》)。因此,我认为《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
至于《五藏山经》《海外经》等九篇,则情况略有不同,它所说的“天下之中”虽也包括了巴、蜀地区,而同时却也包括了荆楚地区,这部分就很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作品了。
前面谈过,《海外经》与《海内经》对四方方名的排列顺序与当时中原传统以东、南、西、北为序者不同。这个不同的序列我们在屈原的《远游》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可以找到旁证。《远游》叙其偕仙人周游天地时,先言“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继言“嘉南州之炎德”,显然是从南开始。次言“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句芒,东方之神,太皓(即太皞),居于东方,这是由南而东。次又言“凤皇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蓐收为西方之神,是又转向西方。次言“吾将往乎南疑”,“祝融戒而跸御”,是拟由西南而不果。然后言“逴绝垠乎寒门”,“从颛顼乎增冰”,这是由西而北。司马相如《大人赋》是模拟《远游》,它先言“祝融惊而跸御”,次言“使句芒其将行”,是由南而东。次又言弱水、流沙、昆仑、三危、西王母,这些都在西方,又次言幽都、北垠、玄阙、寒门,是又由西而北。都是由南开始,由南而东,又另由西而北。这和《海外经》内地理排列顺序是基本相同的。而张衡《思玄赋》则不同,篇内虽也写了《远游》的历程,但它的路线却清楚地是以东、南、西、北为序。《远游》作者屈原是楚人,《大人赋》作者司马相如是蜀人,且系摹拟《远游》,故其游历路线同于《远游》。《远游》与《海外经》的这一相同之点,也可以作为《海外经》作于楚人的旁证。
三
关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问题,自刘秀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它是大禹、伯益所记。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司马迁曾见到过它,《淮南子》曾引用过它(主要见于《地形》),《吕氏春秋》也曾引用过它(见《本味》《求人》等篇);同时,从它的内容来看,多言神怪而又没有什么带思想性的东西,这和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比较起来,大不相同,这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或者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区)所记叙的远古传说之辞,而不可能是秦汉时期文化已相当发展、交通也相当便利的时代的产物。其为先秦时代的古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究竟是作于先秦何时呢?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中山经》说:“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说:“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在这两条南北流向同注于黄河的水道之间,还有器难之水、太水、承水、末水等,据《中山经》的记载,这些水道都是注入役水的。但据《水经注》的记载,这些水都不是注入役水而是注入渠水,甚至连役水也不是注入黄河而是注入渠水。但《水经注》所说的渠水却又不见载于《山海经》。两书这一差异不可不说是相当巨大,而这一巨大的差异却正有益于探讨《山海经》的时代问题。我们知道,《水经注》所说渠水,就是战国时的鸿沟。鸿沟是在战国时梁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才开凿的。古役水注河之迹,以及役水如何改注渠水,器难等水如何改注渠水,现已不可详考,但这一巨大变化之所以发生,当正是由于鸿沟开凿之故,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中山经》之所以不载渠水,以及所载上述流注之所以不同于《水经注》,正说明《中山经》的写作时间是在鸿沟开凿之前。因此,我们认为《五藏山经》这部分的写作时代不能晚于梁惠王十年。又《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太行山脉区域的水道,都是黄河西北的水道。载有:“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又载:“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据胡渭《禹贡锥指》的考证,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改道之后,太行山区域的水道才有注入黄泽的可能。《北山经》既载太行区域的薄水、明漳水注入黄泽,正说明《北山经》的写作时代不得早于周定王五年。准此两点,我们认为《五藏山经》的写作时代当在周定王五年至梁惠王十年之间(公元前602—前360年)。同时,黄泽一名不见于春秋时代,而只见于战国,则其写作年代应当是更靠近于梁惠王十年,其写作时代是比较晚一些。至于《海内经》与《大荒经》两部分的写作时代则可能较早。《海内东经》说:“巨燕在东北陬。”《海内北经》又说:“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海内西经》又说:“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燕灭之。”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是不很强大的,不配称之为“巨燕”。此经载其南有列阳,东北灭貊国,其土宇相当辽阔,这应当指的西周时代的燕国。《海内经》不仅称燕为“巨燕”,同时也称楚为“大楚”(《海内东经》)。《史记·楚世家》说:“熊渠当周夷王之时,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后十世至若敖,而霄敖,而蚡冒,相当于周幽王、周平王时代。《左传》沈尹戍说:“若敖、蚡冒至于文、武,地不过同。”“同”是百里,西周末年楚为百里之国,不能称之为“大”。“大楚”也当是指西周时能立三子为主的时代。从《海内经》称燕、楚为“巨燕”“大楚”来看,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当是写作在西周中期以前。《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关于“西周之国”一语需要作些解释:《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既云“天下之中”,又云“西南”,本不相妨,是知地在“西南”而仍保留了“天下之中”的传说。“西周”是指王畿千里之地的关中一带为周国,它还没有把燕、齐、晋、楚等国都认为是周的疆土。古代认识是如此,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是如此。即如《尚书·多士》说“用告商王士”,是在周已灭商之后,周人对它所封商的后代仍称为“商王”。诸侯的土地即天子的土地,古人尚无此种大一统的观念。所谓“西周”“北齐”是因为古人对于方位的认识本不一定准确,《山海经》本书多处是如此,至于分平王以后为东周,平王以前为西周,那是后来的习用语。〗《大荒北经》又载:“有北齐之国,姜姓。”这都说明这部分的写作年代不能早于西周。但与此同时,周在东迁以后,失去了关中,也不可称之为西周之国,也不能把它记载在《西经》之内。因此我们认为《大荒经》部分的写作时代当在周室东迁以前。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尽管它所记载的这些古代帝王包括了后世所说的三皇五帝:如太皞、女娲、共工、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而《山海经》中却绝无任何三皇五帝系统的痕迹。同时,这些人物多被描写为神话中的人物。这都正说明《山海经》的写作年代是较早的。当时还没有把神祇降为人帝,更还没有把古帝王组成三皇五帝系统。根据我从前的研究,五帝之说,始于齐威、宣之世的邹子五运之说,三皇之说更在此后(详《古史甄微·三皇五帝》)。以此而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也不能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邹子五运之说兴起之后。
我们且再从《山海经》三部分的内容来考察其时代。《大荒经》部分所记神怪最多,应当说是时代最早的部分(或者是文化更落后地区)。《海内经》部分所载的奇异较少,应当是时代稍晚、文化稍进时的作品。《五藏山经》部分就更雅正一些,应当是最晚部分,或者是经过删削润饰的作品了。但是,《五藏山经》的写作时代虽较晚,而它保存了不少很古的流传。《五藏山经》中记载了不少动物在医药上的性能。如“鯥……食之无肿疾”,“赤鱬……食之不疥”(《南山经》),“肥遗,食之巳疠,可以杀虫”,“溪边,席其皮者不蛊”(《西山经》),等等。神农尝百草而著《本草》的传说,表明草木的医药性能是采集或农耕时代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则《山海经》的这类记载,便应当是狩猎或畜牧时代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了。我们再从《北山经》所载地理情况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它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况,其地理时代远在《禹贡》所反映的地理时代之前。根据我过去的研究,历史上渤海海岸的变化,由于地盘升降的影响而有着日益向西扩展的趋势(详见《古地甄微》)。《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碣石山在辽西临榆县南水中。”郦道元注说:“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郦道元的说法,已接触到了这一变化趋势。据《水经》的记载,说明在写作《水经》时碣石已在海中,是海岸当在碣石西。而文颖注汉武帝“东巡海上至碣石”时说“此石著海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可知西汉前期碣石虽已沦海,但还近在海旁。而在《禹贡》写作之时,则碣石显然犹在陆上而尚未沦海。故它一则说“夹右碣石入于河”,再则说“导岍及岐……至于碣石入于海”,都说明碣石是滨海之山,河水经由碣石而入海。则海岸当在碣石之东。而《山海经》却说:“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出于碣石的绳水既东流而始注于河,则河之入海当在更东,而海岸无疑的也当在更东地方了。胡渭把“东流”改为“四流”注于河,是没有根据的。这一地理情况显然是远在《禹贡》所载地理情况之前。到秦汉时代海岸已西到章武了。假如我们认为《禹贡》所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则《北山经》所载这种地理情况就更久远得多了。
吕子方先生说:《大荒东经》载有“日月所出”之山六——合虚、明星、鞠陵、孽摇頵羝、猗天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载有“日月所入”之山六——方山、丰沮玉门、日月山、鏖鏊巨、常阳之山、大荒之山,完全是两组对称的山头。用山头来记载“日月所出”“日月所入”,是用星象为历法的科学还未发明之前的一种原始历法。吕先生这个说法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同时,这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山海经》保存了很多上古时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在前面虽曾推断《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前期,但它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
我们在上面肯定了《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因而它也和其他很多先秦古籍一样,在流传当中常为后人所增削窜改,既有散佚,也有增入。如《山海经》古当有图,陶潜就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郭璞作注时也还见到图,故在注中有“图亦牛形”(《南山经》)、“亦在畏兽画中”(《西山经》)等语;而且还另有《图赞》。山海经的这个图,其起源应当是很古的。王逸序《天问》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天问》之书既是据壁画而作,则《山海经》之图与经其情况当亦如是。且《天问》所述古事十分之九都见于《大荒经》中,可能楚人祠庙壁画就是这部分《山海经》的图。至于《天问》与《大荒经》的出入之处,这应当是楚人所传壁画与巴蜀所传壁画的差异。《后汉书·笮都夷传》说:“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灵海神,奇禽异兽。”《山海经》部分为巴蜀之书,此笮都图画可能即《山海经图》之传于汉代巴蜀地区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寳诣之象。”也可能部分是沿袭《山海经图》而来。《天问》是始于天地、日月,笮都图画也是始于天地、日月,应当不是偶然的。南中之事恒传为诸葛,是否确为诸葛所作,已无法查考。即令是事实,诸葛也未必全是凭空想象,而应当有所依据。但是,《山海经》的这部古图,却早已散失,现在流传的图,是后人所画。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山海经》是既有散佚又有增补的。
前面曾谈到过《汉志》所载《山海经》只十三篇,今传本却多出五篇,应当是刘秀校书时所增,这是整篇整卷增补的例证。至于篇内之增入者当也不少。如现行本中所载地名多与汉代地名相同(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海内东经》后段所叙二十六条水道中),故而有人提出《山海经》写作于汉代的说法。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山海经》最晚部分也当写作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因此我们认为《山海经》这些部分当不是原来所有而是后人的附益窜改。《颜氏家训·书证篇》说:“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曁,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后人所羼,非本文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所谓“后人所羼”是指哪些东西?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我们认为这类羼入,一般只是具体地名的羼入,而不是带有这类地名的记载全条都是后人所羼。如《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条中的“在长沙零陵界中”七字显然为后人所加,其痕迹非常清楚。又如《海内东经》所载各水道,所载地名多在流注之后,也显然为后世所加。如:“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长州。”“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等等。衡以全书他篇所载山水(如《五藏山经》)的体例,则上文中的“高山在城都西”“在长州”“余暨南”“彭泽西”等语,都当是后来所附。这一类的附语,应当是传写时所加注的当时地名,因辗转传钞而误入正文了。第二,这一类地名虽很多与汉代地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地名始于汉代。秦汉郡县之名大多沿袭战国旧名,如朔方、雁门、上郡、琅琊等之类甚多。更何况《山海经》中这类地名中还有一些是汉代所不可考见者,如《海内南经》的湘陵、丹阳,《海内西经》的高柳,《海内东经》的聂阳、雍氏之类,因此一概认为是汉代地名是没有根据的。第三,把《山海经》这类地名取以与《汉书·地理志》比勘,则可发现其用法不能契合,而《山海经》所载当为较早时期的情况。如海内东经(以下省称《经》)载:“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而《汉书·地理志》(以下省称《志》)载:太原郡汾阳县,“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志》河东郡有皮氏、汾阴二县。《经》说是皮氏入河,《志》载为汾阴入河,并不是因为河道改易,而是由于郡县分合。郡县设置的规律一般是愈后愈密,愈后愈小,原为皮氏一县,后又分皮氏置汾阴。《经》记皮氏而《志》载汾阴,正说明《经》的时代在前而《志》的时代在后。又如《经》载:“沁水出井陉山东,东南注河,入怀东南。”而《志》载沁水至荥阳入河。按《志》河内郡有怀县,河南郡有汤县,两县毗邻。《水经》云:沁水“东过怀县之北,又东过武德县南,又东南至荥阳县北,东入于河”。也当是先为怀县一县之地,后分为数县,有武德,有荥阳,也正说明《经》所载当在未分县之前。《山海经》所羼入之后世地名多属此类,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这样分析只能说明《山经》早于《汉志》,而其具体时间则由于分县之时不可考而难据以推求。因此不得不从另一途径来进行探寻。考《经》载:“沅水山(当衍)出象郡镡城西。”按象郡之设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扬越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南越列传》),则此等地名之羼入时间当不得早于始皇三十三年。此《经》称“象郡镡城”,而《志》以镡城属武陵郡,考《汉书·昭帝纪》,元凤五年秋罢象郡,《水经·沅水注》:“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应该是镡城原属象郡,后置武陵郡而镡城遂自象郡改属武陵。此《经》言象郡镡城,知此等地名之羼入当在汉高置武陵郡之先。又考《海内经》载:“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而《志》载九嶷山在零陵郡营道县,《经》不言“在零陵营道界”而言“在长沙零陵界”,应当是当时的零陵还没有设郡,还只是长沙郡的一县。考零陵在未设郡前属桂阳郡,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才分桂阳设零陵郡(见《志》及《水经·湘水注》);而桂阳郡又是在高祖二年才从长沙部分出(见《志》及《水经·耒水注》),只有在桂阳还没有从长沙分出单独设郡时,零陵才可能属于长沙。《经》既称“长沙零陵”,就说明了其羼入年代不得晚于汉高二年(前205年)分长沙置桂阳前。虽然桂阳、零陵二郡后都曾并入长沙国,也可能因此而称为“长沙零陵”,但《经》又载“泾水……北入渭,戏北”,考《志》不载“戏”名,而《史》《汉》的《高帝纪》却两次出现“戏”地:“周章军西至戏”,“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索隐引文颖云:“戏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说明秦时确有戏地。新丰是高祖七年(前200年)所置,当是新丰置后而戏之名逐渐隐,故志不载。经称“戏”而不称“新丰”,当是在新丰未置之前。就是说,羼入年代之下限纵不晚于高祖二年,也当不晚于高祖七年。综上所说,我们认为《山海经》的这类羼入部分,其产生时代也是较早的,当是在秦末汉初(前214—前200年)之际。
又如《中山经》篇末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说法与邹衍“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说法相合。《史记·孟荀列传》载:“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如邹子所说,瀛海之内由八十一“中国”构成,如中国之广袤依《孟子》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王制》说“中国方三千里”来计算,则瀛海之内当为七百二十九“方千里”,此数开方,东西、南北当各二万七千里,长短相覆,正与《中山经》所说“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之数相合。《管子·地数篇》《吕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地形》也都说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都当是源于邹子的说法。《中山经》的这段文字,当是后人据邹衍之说所羼入者,也有可能是后人据《管子》或《吕览》之文附入。根据计算,《山经》《淮南》之说很显然是与邹衍相合的。而王充在《论衡·谈天篇》中指责邹衍“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从当时的实际地理知识驳斥邹衍的揣度之辞是颇有理据的;但他说“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就缺乏根据了。他主要是以“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作为立说根据。但西汉儒者都说中国方三千里(都源于《孟子》《王制》),只《欧阳尚书》说中国方五千里。《欧阳尚书》方五千里之说是以《禹贡》五服“每服五百里,合南北为千里”为根据,但五服包括要服、荒服在内,而汉儒常说“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周语》说“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是要、荒为蛮夷所居。“要”是“要约”,是羁縻约束的意思。“荒”是“慌忽无常”,是居处无定的意思。就是说,对此等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族不能如像统治华夏居民一样地来管理,所以说是“不臣”“不治”。既是“不臣”“不治”,当然便不应包括在所谓的“中国”之内。同时,《尔雅》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则蛮夷在东南而戎狄在西北;据《周语》的说法,则东南只有要服而无荒服,西北只有荒服而无要服。这个说法就当时四裔民族来考察,是合适的;周秦以来西北是游牧之族是行国,故说它是慌忽不定,是荒服,而东南则是农耕之族,可以要约羁縻,是要服。显然是西北无要服而东南无荒服,因而认为荒服在要服之外每服五百里而中国方五千里,是没有根据的。王充一代通儒,据此没有根据的说法来讨论邹子和《山海经》的问题,不无疏忽之嫌。同时,即据方五千里之说,在推论计算上也有错误。依八十一分居其一分来算,当为二万五千方里,再以九乘之,又再以九乘之,当为二百零二万五千方里,而充只以九乘一次,以为二十二万五千里,亦为疏忽之甚。
又如《海外南经》篇首“天地之所载……唯圣人能通其道”一段文字,全同于《淮南·地形》,也当是后人所增入者。这一类的问题还多,我们就不多举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整理或使用《山海经》时所应当加以辨析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进而据此认为《山海经》是秦汉时代的作品,那就显然是不妥当的。
总的说来,《山海经》十八篇虽是一部离奇神怪的书,但它绝不能如《四库提要》所拟议的那样,是一部闭门臆造的小说。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它所流传的代表其传统文化的典籍,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子之宋而得《乾坤》,之杞而得《夏时》,巴、蜀之地当也有它自己的作品,《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
此文写毕,与友人讨论谈及,承告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颇有论及《山海经》者,即取粗读一过,其中有与鄙说相合相辅者,亦颇有与鄙说抵牾不同者,但都有参考价值。文中除对《山海经》所载帝俊、黄帝、颛顼的次数改用徐先生的统计外,余皆仍旧。望读者自行查考。(文通附记一九六二年元旦)
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