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疆文教治策是历史时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元、明两朝基于对西南地区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等多重因素所造就的特殊边疆属性的深刻认识,在对当地实施治理的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文教治策,构筑起以庙学为主体的边疆文教体系,希冀实现形塑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治边目的。边疆庙学从精神层面建构了边疆社会与内地一体的精神堂奥,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的重要缩影之一,为科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儒家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苑鑫,男,河南淮阳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史地。
厉行边疆文教是中国古代形塑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认同意识的主要路径,各朝统治者均将施行积极的文教治策视作推进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希冀在民族多元互动过程中形成族际儒家文化认同[1]。元明时期的西南地区【本文中的“西南地区”概念,取自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厘定的历史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今云南省和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市以西广大区域。方国瑜先生指出,“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到明代成立贵州省,又把金沙江以北划归四川省”,“故明代限于云南一省”。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治理,在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元、明两朝统治者的民族身份虽然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地奉行崇儒重道这一基本国策,面对纷繁复杂的边疆形势,均通过积极的边疆文教治策提升西南社会对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具体措施包含“礼分华夷”“怀柔远人”的礼仪制度,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为主要手段[2]。依此而言,作为儒学辐射平台的庙学自然成为元、明两朝推行边疆文教治策的实践主体。庙学即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根本的教育理想的物化象征,“古者,国家造士之所皆曰学,又曰学宫,后世以其庙祀孔子,故曰庙学”[3]467,指代地方上学宫与孔庙一体创设的、以传播儒家文化为目的的学校。
目前学界对元明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教治策给予了较多关注,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首先,部分通论中国古代治边策略的相关论著,整体考察了作为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治理政策之一的文教治策的厘定过程,探究其治边依归和演进脉络【代表性论著有:方铁《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高福顺《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贾益《礼仪文教与边疆治理:德化政治中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3期;蒋金玲《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明代边疆文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为全面认识元明时期文教治策在西南地区的具体实践奠定了基础。其次,从不同视角考察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实践的具象化表现——官学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学官群体、科举制等内容【这类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申万里《元代庙学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沈海梅《明代儒家思想在云南传播的主要途径——官学教育》,《孔学研究》1995年第1期;陈庆江《明代云南府州县儒学考论》,《学术探索》2000年第5期;王立平《元代地方学官》,《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刘淑红《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提学官制度》,《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其中庙学的设置和区域分布备受关注。不过,全局性考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内在逻辑的成果并不多见,划分时段的考察方式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对元明时期文教治策演进脉络的整体性审视。最后,部分成果基于文教治策实践的视阈,考察儒学传播与西南社会嬗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类成果多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赵旭峰、路伟《文化认同与多民族国家统一——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4期;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林超民《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蔡亚龙《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张锦鹏、钟行《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学术探索》2023年第11期。】。遗憾的是,相关论著对推动儒学传播和儒家文化认同形塑具体路径的微观分析稍显欠缺,从而导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的阐释深化着力不足。本文拟以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为考察对象,将文教治策的具象化形式——庙学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文教治策在西南社会培育以儒学为思想根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并总结边疆社会对积极向化的反馈,以期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的研究。
一、“崇儒重道”:西南地区文教厘定的历史背景
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民族构成多样,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鲜明。以云南为例,“云南自古羁縻之地,而不通于中国之法,盖其犬羊之性,顺之则臣,逆之则叛,势使然也”[4]754。上述因素造就的特殊边疆属性是中原王朝开展西南治理的出发点,推行积极的边疆文教治策成为元、明两朝一脉相承的施政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厘定根植于中原王朝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蒙古人对儒学的接纳与耶律楚材存在密切联系,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因提倡儒学而深得赏识。不过,那时的蒙古人正忙于四处征服,汉地未受重视,有蒙古贵族就认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5]832。在这一背景下,儒学并未对蒙古的国家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窝阔台继承汗位后,耶律楚材以经营汉地可增加税收之实际操作博得信任,随后“以儒道进说,并请恢复汉地秩序及安辑士人”[6]102。耶律楚材为提升儒学和儒士地位奔走呼号,先“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又遣人找到孔子后人“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再“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7]3458-3459,文治始兴。平定燕京后,宣抚使王檝以金之枢密院为宣圣庙,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太宗六年(1234),窝阔台“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命贵臣子弟入学受业”[7]2032。至此,儒学在蒙古国家政治场域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为元朝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确立奠定了政治根基。
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以忽必烈在以“汉法治国”的过程中对其十分重视[8],进一步推行儒化政策的忽必烈成为蒙古政权性质的转关者[9]。事实上,忽必烈早在潜邸之时就广揽四方文学之士,以之作为未来“大有为于天下”的政治资本。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受命主治汉地,其间延揽了更多儒士,并力图以汉法治理汉地[10]296。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后发布《中统建元诏》:“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5]106经过朝臣儒士多番不懈努力,儒学终成国家政治正统,而天下一家、不辨华夷等观念的宣扬消弭了传统的“严华夷之辨”的消极影响,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基于此,后世称赞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7]377。
面对汉人儒士对蒙古人入主中原正统性的质疑,业已上升为治国理念的儒家文化认同遂成为元朝建构政权正统性和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理论支撑。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曾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进行颠覆性阐释,以服务于元朝政权正统性的构建,其言曰:“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晋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11]211郝经认为政权正统性在于是否秉持儒学所倡之“道”并力行之,无关统治者的“华夷”身份。此后,姚枢提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华”[7]3064的建议。面对诸路学校久废而无以育成人才的不利局面,忽必烈于中统二年(1261)下诏置天下诸路提举学校官,“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据某人可充某处提举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12]12。蒙古名臣赛典赤与儒学渊源颇深:宪宗三年(1253)奉令增修燕京国子学,后来儒道围绕燕京国子学发生争端,忽必烈令赛典赤裁决[13]200。不难发现,忽必烈命赛典赤裁决燕京国子学争端,除基于信任外,其人“崇儒重道”的个人情感亦应在思虑范围之内。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出任云南平章政事,锐意革除兀良合台为政时期的军事遗弊,“下车莅政,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凡兴利除害之事,知无不为”[7]3064。赛典赤为扫清云南地区文教事业发展障碍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乃损俸金市地于城中之北偏,以基庙学”[14]24,“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7]3056,西南边疆文教由此滥觞。赛典赤去世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7]3066,“用夏变夷”的边疆治理理念得以延续。
明朝对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明太祖朱元璋奉儒学为圭臬,早在元末征战中就曾数次亲至文庙拜谒。在自身正统性的建构上,明以元为“天授”正统,并不否认蒙古“以北狄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只是反对元末君臣的腐朽统治,志在“救济斯民”,从而表明自己是代元而有天下的新朝[15]。因此,以提升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意识这一文教治策并未因统治者民族身份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洪武二年(1369)十月,明太祖朱元璋诏命天下郡县皆设学校,此举可视为其重塑“华夏”的重要一环。《命郡县立学校诏》开宗明义地阐明:“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16]卷四十六在边疆经营方面,朱元璋承袭了传统的“守在四夷”思想,强调“中国既安,守在四夷”[16]卷一百五十三。平定中原后,如何底定边疆并维护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为明朝亟须解决的施政议题。在用兵西南之初,朱元璋就表现出对边疆稳定的关心。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朱元璋谕旨傅友德等曰:“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16]卷一百四十二次月,朱元璋再次谕令指出:“夷性顽犷,诡诈多端,阻山扼险是其长计,攻战之策,诸将军必筹之熟矣。若顿师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胜,乘机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可也。”[16]卷一百四十三频繁诏谕反映出在朱元璋的认知中,西南地区实现“一举而定,再不劳兵”是战略目的,从而间接促成明朝“文教以化远人”的治边策略。西南甫定,朱元璋即谕云南布政司各府、州、县皆置学校,并令“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17]559。遵循“广教化,变土俗”的政治依归,明朝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不断建构边疆社会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形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明朝以边疆文教推进边疆治理的理论基础。洪武一朝奠定的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成为有明一代诸位帝王持续遵循的治国典范。
二、移风易俗:地方官员有关庙学教化旨趣的理想表达
自元以降,广袤的西南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辖之下。在元明时期边疆文教的实践历程中,庙学俨然化身为沟通“官”与“民”的桥梁,成为官方向民众传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的平台、儒家文化的辐射源[18]。通过庙学播衍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以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礼仪规范,在边疆社会培植“大一统”政治认同的历史文化根基,成为元、明两朝统治者共守的边疆治理理念。事实上,无论教育形式还是教学内容,西南地区庙学与内地庙学并无二致,均采取日行课业的师生授受方式,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科举考试为导向,将为国培养治术之才作为最终目的。不过,若从地方官员对西南地区特殊边疆属性的认知出发,庙学制在边疆的铺展则凸显了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的另一种意蕴。
元朝在西南地区设置行省,采取“比于内地”的经营模式。庙学作为行政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一体创设,“署省台以控驭之,置郡县,设庠序,宣教化,布政令,移风易俗”[14]35。但是,初附之际西南地区部族林立,离心势力炽盛且根深蒂固。至元元年(1264),僰僧舍利畏联合罗罗、白蛮等部族起义,拥众近30万人。舍利畏狂妄叫嚣:“蒙古系北虏,吾等南蛮,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19]241舍利畏口中的“北虏”“南蛮”说辞,源自“中国、戎、夷、五方之民”这一先秦时期区分不同族群的经典表述,即《礼记》所谓“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20]359-360。舍利畏起义不但凸显了元初西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对元朝实现疆域“大一统”的消极影响,而且折射出元初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巨大困境。
基于此,为弥合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差异,营造“华夷无间”的边疆大治局面,地方官员在实践中原王朝边疆文教治策时往往有所倚重,十分强调以“周孔之道”涤濯异俗,作为宣扬官方意识形态媒介的庙学因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施治手段。至元十三年(1276),中庆路学竣工落成,郭松年为之作记,在文末感慨道:“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风以资于闻见也,又非乡党师友之习也。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见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材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则任斯事者,宜无愧于文翁云。”[14]24-25值得注意的是,郭松年曾两次游历西南地区,收集沿途见闻后撰成《大理行记》,对边疆人文风貌和文化习俗有较为深刻的体察。因此,郭松年对中庆路学促进边疆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有着清晰认知,故而在记文中寄语“任斯事者”以“举中国之治”为己任,言辞间透露出以庙学播衍“夫子之道”、以文教凝聚边疆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实现边疆稳定的美好愿景。至元二十四年(1287),大理路庙学竣工,路学教授赵辅弼属文记其事,追溯了边疆文教治策的演进脉络。寻常例而言,大理是西南地区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南诏时期即有“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17]757的记载,大理时期又有“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21]165的典故,儒学积淀不可谓不厚重。不过,在深谙文教意涵的赵辅弼看来,彼时“礼乐衣冠皆未得其正”,转而将郝天挺倡办大理路学视为历史空前之盛事,称赞其“使旧染之俗,咸与维新,此嬴秦之所绝无,汉、唐、三国、六朝之所未见”[3]229。较之前文引述郭松年一文,赵氏之文用意十分明确,旨在将儒家之“声名文物”“礼乐纲常”塑造为各民族的日常准则,通过中华文化对边疆社会的浸润,达到“使被毡裘,化为典章”的目的。
大德元年(1297),肃政廉访使王彦作文记中庆路学兴建御书阁一事。在记文中,王彦针对边疆世居民族彪悍好斗的性情直言不讳,认为“天下之不一,亦且教养有所施而文化行,非若齐、鲁之变而至于道之易也”,继而又言“国家之有大造于兹土,以开群蒙之天者,亘有鲜闻”[14]385。至治二年(1322),完成出使安南使命的奉议大夫、礼部郎中文矩于返京途中游历云南,访中庆路学有感而作《题中庆学庙壁》一诗。诗文流宕尚气,不但描绘了一幅借由文教治策的深入实践而实现华夷一家、安定祥和的边疆图景,而且昭示着地方官员的孜孜追求:“滇南古荒服,荐祼岂异礼。王宫正南面,温厉思敬止。豆笾俱威仪,登献何。升歌永齐商,琴瑟散宫徵。共言唐法曲,岁久复惉懘。陋邦何足征,居夷圣所儗。于皇人文化,道大孰与比。六经如日月,洞照无远迩。叙秩敦彝伦,百王同一轨。邈哉天何言,悠悠政如此。”[14]351
平定西南地区后,明朝参照内地模式构筑西南地区行政体系,先置布政司、府、州、县以治之,又诏西南地区各府、州、县兴举庙学。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通过构筑完备的西南地区文教体系,以期将边疆社会纳入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明初的西南地区并非一片乐土,当地先有奉北元为正朔的故元梁王残余势力的负隅顽抗,后有末代大理总管段世“我云南僻在遐荒,鸟杂犷悍,最难调化,历代所不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语言不通,嗜欲己异,得其民不可使故也”[22]2093的分裂自辩。在消灭梁王残余势力后,傅友德针对段世的割据企图,以“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17]764之语斥之,彰显了明朝实现疆域“大一统”的坚定决心。边疆底定后,厘定积极的边疆文教治策成为朱元璋迫在眉睫的治边要务,在边疆社会培育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认同已然成为明朝的施治方略,为历任地方官员所遵循。
洪武年间(1368—1398),西平侯沐英命人立石雕刻《太极图》于云南府学,并勒《白鹿洞规》于碑阴。时任左布政使张紞作《题〈太极图〉〈白鹿洞规〉后》一诗,在寄语中感叹“今表而出之,开先斯人,俾知务本而守要”,“吾知椎髻之弊、鼓刀之习可以渐革,而天理、民彝焕乎日著,施愈博而泽愈远”[14]11-12,申明了以庙学传播儒学的教化旨归。张紞于洪武十五年(1382)受命任职云南,朱元璋在其临行之际特意嘱咐:“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兴之所然。且云南诸夷杂处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诚可会人,朕之生灵是幸。”[17]556上引“渐革椎髻之弊、鼓刀之习”之语所蕴含的鲜明“用夏变夷”思想,应源于张紞对西南地区的深入了解,从而构成了张紞不遗余力推崇以边疆文教实践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正统年间(1436—1449),明英宗为革除儒学教育流弊,特置提学官以董一省学务,提学官群体对边疆文教治策和治边旨趣的认知亦值得关注。弘治年间提学彭纲评价道:“在古,云南之人悍诈好杀,历代不能臣。我国家用之,一变其俗,至于淳实忠顺,奔走而服役,百数十年来怡熙恬睦,与中夏埒。是固由华风渐被,列圣陶范之所致,而其敷施之端,亦以学校之设,有以明人伦,昭文治,训其子弟以及其父兄亲党也。”[23]无独有偶,万历年间任职的提学邓原岳亦有类似表述,其在寄语诸生时指出:“今士生右文之世,不由户而得师,何论汉德?故被服圣教则为良士,沐浴圣化则为良臣。毋自毕其气,毋自隳其节,期以用夏变夷,较然不负其所学,则其惟诸大夫借以荣施。”[24]693彭、邓二人的着眼点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边疆文教治策,不但肯定了其在施行国家教化、传播儒家文化、弘扬价值理念和礼仪规范的社会价值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且凸显了边疆文教治策在推进具有“大一统”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元、明两朝厘定之边疆文教治策成为西南地方官员世代遵循的施政准则,地方官员往往将之视为“仰体”以“圣天子”为象征的王朝国家崇儒重道治国理念的体现。循情而言,地方官员读书业儒起家,科举正途出身,对儒学往往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反映在日常设政施为中,“固有心领神契而继序不忘者,则于兴孔子之庙之学,以振起而光大之也”[25]760。以上胪列之关于边疆文教旨趣的表达代表了多数西南地方官员的认知,“不以学校为急务者,有司之责也”亦成为地方官绅阶层的共识,边疆社会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空前高涨。
三、“风化由出”:庙学铺展与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实践
庙学乃为国储才之地,风化由出之源。高明士指出,“学校教育透过‘庙学’形制的规范,使为师者身兼经师与人师,可视为圣贤的化身,学生学习的榜样;而学子平时与庙中圣贤为邻,又瞻仰为师人格、学问,乃体会步登圣贤堂奥之境是有可能的”[26]30,46。初创于元代的边疆庙学在西南地区教育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文学传播于云南,自秦汉以来有之,南诏大理时亦盛,惟建孔子庙实始于元初设行省之时,为创举也”[17]269。西南地区的庙学在初创时,即被中原王朝和地方官员赋予了培养边疆各族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和“大一统”政治理念认同的使命。可以说,边疆庙学的铺展不但反映着西南地区文教治策实施的历程,而且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脉络。
元代学制已较为详备,地方设有路学、府学、上中州学、下中州学、县学,“且以国威远震,吾滇兴学亦于此始可纪焉”[3]466。当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诏令天下诸路皆设学置官时,西南地区虽已归附“大一统”版图,但仍处在兀良合台军事体制统治之下,当地并无设学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主持创设中庆路庙学为西南地区兴学之始。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诏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7]2032。至元二十二年(1285),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议事,“恐南方之人逸居无教,风声气习永流于夷毳,由是闻奏朝廷,令各路设教官、建儒学”[3]229,获忽必烈题准。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再诏云南各路建学,“教官以蜀士充”[7]362。在“兴学校,渐风化”的政治依归下,元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积极运筹,边疆庙学的创设相继展开。
遗憾的是,元代西南地区庙学的确切数目已失于史载,仅能通过排比胪列诸部省志相关记载粗略估计其规模。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当地元代共设中庆、临安、大理、徵江四所路学和安宁、嵩盟、石屏三所州学。其中,除中庆路学外,临安路学由宣抚使张立道创建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大理路学由参知政事郝天挺倡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徵江路学由总管魁纳创设于大德年间(1297—1307);安宁州学创设于大德六年(1302),嵩盟州学由同知阿罗哥实里荡倡建于至正八年(1348),石屏州学亦创置于至正年间(1341—1370)。《正德云南志》较《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增加河西县学的内容,记述其创设于泰定年间(1324—1328)。《万历云南通志》在《正德云南志》基础上增添鹤庆路学的内容,而未言其创置时间。《雍正云南通志》在《万历云南通志》基础上增加永昌府学、邓川州学的内容,且言永昌府学在都元帅府西、邓川州学在中所会真寺后【参见陈文纂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刘景毛等点校,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雍正云南通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第5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上引各志均漏载明初改隶四川之建昌路,该路庙学创设时间未详,仅知其址在“都司治西南隅”[27]。由上述引文可知,元代在西南地区设置的庙学至少已达12所。如前所述,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至元年间两次下诏命令西南地区各路建学置官,当时这一地区聚集了一众深谙“用夏变夷”思想、以在边疆形塑“大一统”政治认同为个人抱负的官员,除赛典赤外,倡建临安路庙学的张立道、捐修大理路庙学的郝天挺等人均为其中杰出代表。赛典赤去世后,“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领省事,一时参佐皆中州士大夫”[14]24。在此背景下,元代西南地区庙学的建设规模之小似与情理不符,难免令人对当时西南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状况产生质疑。事实上,若广泛勾稽史料,便可窥见元代西南地区庙学真实规模之一斑。
按照元制,各级地方逐级建学置官,“路教授拟设一员,学正、学录各设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12]139-140。教官的分级设置,为考察边疆庙学的创设情况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支撑。据元人邓麟所撰《元宣慰副使止庵王公墓志铭》记载:“先生讳昇……时选官翰林修撰文子方一见器之,遂铨仁德府儒学教授……源道参滇省大政,举为曲靖宣慰司教授,庠序大振,追复学田,生徒百数人,成才者夥。秩满……会瀛山范公佥新南宪,调儒学提举,朝廷准授文林郎,葺旧庙,兴废学,第见功効……选充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14]414通过墓志所述王昇的宦迹,可知元代西南地区的设学情况:中庆、大理、鹤庆等路和永昌府等处庙学的创设得到印证,曲靖路、丽江路、姚安路、威楚开南路和仁德府、镇南州等处庙学创设的记录可补史载之阙。由李敬仁所撰《追为亡人杨昭宗神道》,可以证实元代在大理路蒙化州也曾设学置官:“(上阙)彦诚,号复斋……故云省平章□□□□□□□路侯时惧其宗属子侄,逸居无教,请彦诚正蒙化州学训,州牧段信苴兴□生礼义,□□□教有方。”[28]元人李源道撰《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记载昆明人王惠于延祐六年(1319)调任仁德府为美县尹,在任时“兼劝农事,修孔子庙,以馆来学”[5]784,据此可知为美县在元代已经开设庙学。此外,散见于地方志书中的相关史料也值得关注。《新纂云南通志》收录《狮山建正续寺碑记》撰者署名“武定路儒学教授昆明杨兴贤”[3]253,明代中期的《栖贤山报恩梵刹记》碑署名撰者为“永昌府儒学教授华阴杨森”[29]。上引两则史料充分说明,武定路和永昌府在元代均曾建学。至正年间(1341—1370),都元帅阿喇帖木蒙古右旃亦曾建文庙于驻地曲陀关,时人赞曰:“阿喇帖木蒙古右旃为边将,披坚执锐,驰骋游猎,分内事也。今崇尚斯文,投戈讲道,能为人之所不能者,非有高世之志,绝伦之才,其孰能之?”[3]292元代西南地区的庙学至少22所,与后世“中庆诸路建学几遍”[24]275之描述相差无几。需要说明的是,西南地区特殊的边疆属性显然对庙学的广泛推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滞。元代西南地区庙学的普及率约仅为14.69%【庙学普及率=庙学数目/行政区划数目。元代云南行省行政区划总数为143,取自《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中“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的记载,计算云南庙学普及率约为14.69%。】,与全国71%[30]的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透过庙学的普及程度,可以看到元代西南文教治策实施的不尽完善之处,因而后人叹曰:“滇南风气,至前明始开。”[31]
明朝继元朝而起,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推崇庙学在行教化、涤风俗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制度草创时即诏令天下郡县皆置庙学,奠定了有明一代广厉文教的施政基调,史称“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学制详明,为历代最。其学科之扩充,学规之严密,皆较优于历代”[3]466-467。遗憾的是,因受朝代更迭和兵燹频繁等因素的影响,创设于元代的庙学沿至明初时多已毁坏无存,这正是明代志书中记录西南地区庙学数目寡少的原因之一。西南初附,明代的庙学铺展先在滇中滇池流域、滇西洱海流域和滇南等社会经济素来发达的区域实施,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诏置云南大理府、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诏置云南、楚雄二府儒学。为维护边疆稳定,明朝在西南地区推行都司卫所制度。在土司地区设学一直处于朱元璋施政理念之中,早在洪武十五年诏谕入京朝贡之普定土知府时,就向其提出令土司子弟读书业儒的设想。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朱元璋的这一文教治策计划终于付诸实施,诏令西南地区各土司设学[16]卷二百三十九。在土司地区设学有着以治边为出发点的政治考量,“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置学设官后“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理、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6]卷二百三十九。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又将土司承袭与接受儒学教育相关联:要求“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32]7997。明朝的一系列举措既体现了边疆文教治策以边疆治理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又反映了中央政府试图将西南社会纳入“大一统”版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努力。
不过,明初厘定的边疆文教治策却对卫所子弟入学造成诸多不平等,“文武官舍军校匠余,悉不许于外郡入试”[33]。因为明朝对军事移民实行军户制度,军户子弟成年后子承父业,履行戍守边疆职责,入学后无法享受廪膳待遇。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宣德十年(1435),明宣宗才参照府州县学例,“诏天下卫所皆立学”[32]128,卫所子弟入学读书始有转机。景泰元年(1450),云南提学官姜濬上奏:“各卫所军生,多有人物聪俊,有志于学缘,不得补廪,无人养赡,难于读书。乞不拘常例,军民生员相兼廪膳,庶使生徒向学,不负教养。”[34]卷一百九十二这一奏疏言获得明代宗题准后,庙学才真正向广大军户子弟敞开大门。在此基础上,边疆文教治策的实践渐次在流官治理区、土司地区和卫所驻地展开。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迟至洪武末年,明朝疆域内91.49%[35]102的府、州、县均已设学,而西南地区的这一数字约仅为22.32%【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三记载,洪武年间云南初附时领52府、63州、54县,合计169个政区。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割建昌府及所属8州、3县,德昌府及所属4州,会昌府及所属3县共21个政区归四川布政司;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领2州)3府共5个政区改隶四川布政司;洪武十七年(1384)五月,划云南东川府(领4州)5政区属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普安府(领1州)改隶四川布政司;洪武年间,普定府(领4州)亦改属四川布政司。此外,这一时期朱元璋还对云南布政司区划进行初步调整,裁去5州、14县共19个政区。至洪武末年,云南布政司所辖大约还有112个府州县政区,构成了庙学铺展的基数。洪武年间云南布政司共设庙学25所,这一时期云南布政司郡县区域的庙学普及率约为22.32%。参见苑鑫《“臣民”塑造——元明清时期云南庙学研究》,云南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与前者仍有很大差距。及至明末,西南地区的庙学规模已达70所,造就了“登华舆而坐铃阁者,皆学之出也”[18]之盛景,庙学普及率达到53.68%【明代云南设学政区73个,明末云南布政司区划数量基本维持“十四府、六军民府、二御夷府、一直隶州、三御夷州、三十九属州、三十一县、八宣慰司、四宣抚司、二御夷长官司、三长官司、三安抚司”的建置,另有约二十卫。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6—1141页;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为后续的清朝边疆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庙学普及率的差别说明西南地区文教环境还有诸多亟须改善之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形塑远未完成。
四、华风渐被: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实践成效
在元代以前,西南地区曾长期处在边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统辖之下。在由内地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边疆多以不在场的“他者”角色出现在中原王朝认知之中,通过内部差异性的放大与书写强调“华夷有别”,故多有“不食五谷”“夷狄兽面”等异化形象,建构了僻处华夏边缘的云南边疆的历史与文化空间[36]。在被纳入“大一统”版图之初,西南地区依然族群林立,离心势力十分活跃,严重阻滞“大一统”政治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通过元、明两朝的积极施治,西南地区的文教治策实践取得了诸多值得肯定的成效,为当下正确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奠定了西南地区“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格局
西南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边疆社会的深入播衍,在各民族长期的互动交流中,形成了独具个性、为各民族所共享的一体多元的整体性共有文化格局[37]。自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施行后,“民间俊秀子弟奋发以读书自励,科不乏人,而其父兄亦各向慕,革其旧染矣”[29],培育了西南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格局,本质上反映的是西南地区各世居民族在其历史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冲突、调适和融合的渐进式历程中,建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奠定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实现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根基,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脉络。
作为儒学播衍平台的地方各级庙学,无疑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明代中期云南提学彭纲所言:“自今观之,学校之教,其关系岂不甚重且大乎?在古,云南之人悍诈好杀,历代不能臣。我国家用之,一变其俗,至于淳实忠顺,奔走而服役,百数十年来怡熙恬睦,与中夏埒。是固由华风渐被,列圣陶范之所致,而其敷施之端,亦以学校之设,有以明人伦、昭文治、训其子弟以及其父兄亲党也。”[23]要言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之“一体”奠基于元,形成于明,巩固于清,这样的历史轨迹与文庙建立、推广和兴盛的历史脉络相符[38],凸显了以庙学为主体的边疆文教治策在推进西南地区融入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格局中的积极作用,展现了其对西南地区各民族凝聚、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贡献。
(二)推动了边疆社会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出现
庙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与推行,促使边疆社会孕育了新兴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士绅,推动边疆社会结构与内地渐趋一致,加速了内地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深刻影响着明清以来,乃至今日云南的社会发展[39]。同时,知识分子士绅阶层还是联结官方与地方社会的纽带,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塑造地方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科举兴盛而名闻地方的科举家族,是边疆社会知识分子士绅阶层中的典型代表。在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实践历程中,边疆社会涌现出众多科举家族,如大理府以高昂为代表的高氏家族和以阿天麒为代表的阿氏家族,永昌府以闪仲俨为代表的闪氏家族和以张志淳为代表的张氏家族,等等。这些家族有的是汉人移民后裔,有的是地方簪缨传世的土官世家,抑或是秉承读书业儒家风的少数民族部众,这一群体正是儒学教育推动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维护中华大一统格局的生动缩影[40]。科举家族群体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不但通过修庙助学、提掖后进、赒济贫弱等形式反哺桑梓,而且以著书立说等活动为手段,在边疆社会广为流布蕴含历史文化认同的家国情感认知[41],在西南地区各族民众的心理上逐渐完成共同精神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形塑,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三)“大一统”观念在西南社会获得广泛认同
“大一统”是在西周统治秩序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想,强调“王”的核心地位和以“王”为中心的“天下”政治秩序[42]。元、明两朝属意以边疆文教治策塑造边疆社会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实质,与“大一统”观念所蕴含的政治秩序一脉相承,二者均隐含构建“大一统”王朝国家、塑造“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尝试与努力,高度统一的历史文化认同构成了其共同的文化根基。诚然,“大一统”观念在边疆社会获得广泛认同,历经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与之相伴的是,中原王朝建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坚定意志和对边疆各民族的有效整合,以庙学为主体的边疆文教治策无疑在这一历程中发挥了奠基作用。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实践成效因受特殊边疆属性的影响,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元初僰僧舍利畏发出的“吾等南蛮,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的质疑,与明初末代大理总管段世主张的“俾元元各遂其生,共赏升平之乐”的自辩形成时代呼应,即为其体现之一。随着儒学的深入传播和获得广泛认同,沿至明代中叶,西南边疆社会已经产生“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也”这一饱含“大一统”政治理念的经典认知,并催生了超越单个民族内涵、具有鲜明地方意识和高度历史文化认同底蕴的“云南人”[43]称呼的出现。
“大一统”观念获得广泛认同,底定了西南边疆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历史地位。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腐朽清王朝的封闭大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边疆危机不断深重,西南地区先后遭到英、法两国列强的觊觎。幸运的是,因为西南边疆社会业已塑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一统”观念深入流布并获得广泛认同的背景下,边疆各族人民牢固地凝为一体共同抵御列强侵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为维护边疆安全和国土完整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边地土司恪尽职守,“或鼎革不附,竟以身殉;或遇逆招降,潜逃全节;或因划界,沦入异域,既向当道以泣诉,复怀故国而不忘;或地为强邻所占,而守土负责,不惜牺牲一切以抵抗,并呼号奔走以请援”[3]660。清末至民国时期,云南先后爆发了一系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西南地区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主义热潮:保路运动声讨了英、法等西方列强强占滇省铁路修筑权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丑恶嘴脸;“重九起义”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腐朽统治,声援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恢复了“共和制”,沉重打击了清朝遗老的复辟意图,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抗战时期,云南又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和名闻全国的“民主堡垒”,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与重大贡献。西南地区社会各界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的淋漓抒发,流露出浓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蕴,与元明时期持续开展的边疆文教治策实践和由此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紧密关联。
五、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植根于中华文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意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元明时期西南地区文教治策的实践促进了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塑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紧密的政治关系,奠定了西南社会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格局,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的重要缩影之一。西南地区各世居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互动中增强了对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了边疆与内地共有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历史记忆。这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记忆,最终外化为明代中叶西南地区民众家国情怀的深情流露和近代以来边疆各族民众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边疆安全的坚定信念。我国的辽阔疆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灿烂的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元、明两朝在西南社会形塑“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不但客观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且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1]高福顺.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1).
[2]贾益.礼仪文教与边疆治理:德化政治中的文化认同[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3).
[3]龙云,卢汉,等.新纂云南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孙仁.停止镇守内官疏[M]//万表.皇明经济文录:下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5]苏天爵.元文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6]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王文光,马宜果.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贵州社会科学,2021(10).
[9]姜海军.蒙元“用夏变夷”与汉儒的文化认同[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0]萧启庆.元代史新探[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1]郝经.陵川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王颋.元代史料丛刊庙学典礼(外二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3]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4]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5]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J].历史研究,2022(3).
[16]明太祖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6.
[17]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8]廖国强.文庙与儒家文化——以昆明地区文庙为例[J].思想战线,2008(3).
[19]诸葛元声.滇史[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
[20]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倪蜕.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22]许建平,郑利华.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3]周季凤.(正德)云南志[M].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24]刘文征.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25]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26]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27]李贤,等.(天顺)大明一统志[M].天顺五年御制序刊本.
[28]王云,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下)[J].西北民族研究,1990(2).
[29]张志淳.南园漫录[M].嘉靖刻本.
[30]胡务.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M].成都:巴蜀书社,2005.
[31]谢圣伦.滇黔志略[M].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3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3]申时行,等.明会典[M].万历内府刻本.
[34]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6.
[35]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6]罗群.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与建构——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4).
[37]周智生,张黎波.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历史形成机理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38]廖国强.文庙与云南文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6(2).
[39]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40]蔡亚龙.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41]苑鑫.明代云南的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大理府为中心的考察[J].科举学论丛,2018(2).
[42]李大龙.试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J].西北民族研究,2021(2).
[43]林超民.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J].云南社会科学,2018(6).
《民族学论丛》202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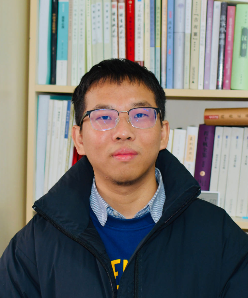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