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明永乐辛卯始设科举。明代云南的儒学家族大都迁徙自中原地区,由于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呈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儒学文化特点。明代云南土司接受儒家熏陶,以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儒学,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多民族融合。学宫、书院及社学的建立拓展了儒学的传播范围,官学与私学、内地与边疆进行多元互动,揭櫫明代云南儒学对于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儒学史意义。
关键词:明代;云南;儒学碑刻;多民族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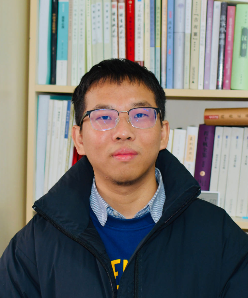
作者简介:赵成杰(1987—),男(满族),黑龙江宁安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石学、《尚书》学研究。
明洪武十五年(1382),大理平定之后,明代统治者在大理实行卫所制度。同时,在元代设立学宫、文庙等儒学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儒学的设立范围,用以培养人才。据统计,云南现存明代碑刻1445块,其中儒学碑刻70块,[1]最早为洪武十八年(1385)杜瑜所撰《浪穹县儒学碑记》,记载大理浪穹县儒学的创建。[2]明代边疆地区儒家碑刻前人少有关注,刘祥学、赵永翔、刘淑红等学者对明代云南儒学的发展进行过综合研究,但较少利用石刻文献二重互证。石刻史料不但能够强化云南儒学的学术认识,也对发扬儒家文化、增强多民族融合大有裨益。
一、儒家碑记所见明代云南儒学之兴起
明朝统治者平定云南以后,治理西南边疆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儒生,突出表现在云南各府州设立儒学学宫。[3]彭时《云南府儒学重修记》(1402)载:“云南古要荒地,自汉以来,虽通中国,而夷气自若。至于有元,行中书平章赛典赤肇建中庆府学,以教化其人,自是稍知去夷而从华。”[4]明代统治者在云南共66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5]
文庙碑、书院碑的记载客观地记录了明代儒学机构的设立。永平县“明洪武二十六年,命临川叶学则为社学师,始建文庙”。[6]洪武年间始建文庙的有晋宁县、呈贡县、太和县、邓川州、浪穹县、通海县、蒙自县等,有明一代云南建造的文庙就有59座,如《重修晋宁州学宫碑记》载“明初晋宁故有学,在州之西北隅,宣德间迁今址”。[7]据统计,明代云南学宫共73所,[8]书院共66所,[9]社学共165所。[10]
云南书院的大规模建立亦从明代开始,姚安《南中书院记》:“明兴,天下郡县多书院,贤出国昌,轶于隆古。”[11]浪穹的龙华书院、大理的苍麓书院都是云南创办较早的书院。康承祖《苍麓书院记》:“……苍麓,弘治十二年,御史关西谢公徘徊形胜而异之,遂于此创席舍焉。”[12]由中原迁居滇省的戍守将领在巩固军屯建设的同时,也建立了书院,传播了儒学,以蒙化封挥最为突出。《敕封文林郎守一封挥墓碑》载封挥“先江西金谿人,宋仁宗时状元及第名尧天者其远祖也。洪武初年高祖希尹因讠是戍蒙化遂家焉……戍师爱之,欲宣内麾下不就,乃力学为郡庠生……建崇正书院,师生教学其中,其田与铁冶给师生及贡举费”。[13]封挥(1457~1524),字本中,蒙化人。据考,崇正书院本为废僧寺,弘治十四年(1501)同知胡光购旧浮屠地建。封挥墓碑又记其门人有雷应龙、徐玹、李茂等人,其中雷应龙(1484~1527),字孟升,明正德甲戌(1514)科进士,先后担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御史等职。
然而,明代前期文庙、书院的发展并不顺利,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明正德十年(1515)五月初六,永胜发生了地震,大理文庙及府学等处发生了坍塌;正德十四年(1519)《重修文庙塑诸贤像记》记录了此事,“正德乙亥仲夏六日,地大震,殿庑倾圮,殿中圣像虽无恙,而四配十哲诸像则皆剥落塌毁过半”。[14]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大理府学到了嘉靖年间才逐步重建、购置图书。杨士云《大理府学尊经阁记》载嘉靖壬午(1522)“宪副彝陵郑公元以提学,至请于巡抚都宪黄岩王,公檄购经史子集若干卷”。又如何俊《修赵州学记》:“赵州乃大理之属,《旧志》里仁乡大路东。元季,遭兵燹。洪武十七年(1384),迁置于三耳山下,其儒学在治之右。洪武十八年,止建明伦堂及三斋。宣德十年(1435),方建文庙及两庑戟门并棂星门。”[15]晁必登《修赵州学记》:“赵州学建自洪武十八年,旧为南向,成化间,以势弗宜,迁之东向……正德间(1506~1521),州守王宗器克敦教事,时提学宪副李公原复以身教为诸生先德行文。”[16]陈谟于隆庆三年(1569)撰写了《参政邹尧臣置学田碑记》,记载赵州儒学的缓慢发展:“赵州之学建于洪武十八年,而向釐于成化,制备于正德,礼隆于嘉靖。各朝骎骎乎贤才辈出矣。而学田未置,若将有所待焉。”[17]大理赵州的儒学经历了从洪武设立,到正德完备,再到隆庆学田设置的过程,反映了明代云南儒学起步较晚、发展缓慢。
云南县文庙的建立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明洪武十八年,云南县学宫建于县之南郭。成化五年,御史郭瑞、按察使曾景迁入城内今地。万历间,知县刘延龄重修。[18]童轩《重修云南县儒学记》:“云南县儒学,肇置于洪武乙丑,垂百年于兹,岁久且弊。成化己丑,巡按云南监察御史文江郭公瑞、云南按察可佥事华阳曹公景按行至县,顾瞻之顷,相与谋而新之,肆令兵民中有误入于辟者,听以金赎。”[19]提学佥事欧阳旦于弘治六年(1493)撰《云南县新迁文庙儒学碑》,记云南县文庙之新迁“弘治壬子(1492)春,佥宪关中周君鸣岐以分巡至,大惧弗任,乃议改图。卜居于卫之左,方得隆址焉。而直偿其主,请于奉敕巡抚都宪华亭张公、巡按侍御安成刘公。”[20]
明代云南儒学家族多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如大理杨氏家族,《故杨公孝先墓志铭》(1363):“上世本华阴人,唐玄宗时,有蛮祐者,从鲜于仲通征云南,军败陷焉。云南王阁罗凤爱其(上阙),累迁崇文馆大学士,兼太傅、清平官。后以劝异牟寻去吐蕃复归于唐,唐封长城郡王,子孙因家云南。”[21]大理杨氏多是随军征战而迁徙入滇,杨氏家族多习儒家经典,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特色。如《故善士杨公同妻赵氏墓志铭》(1465)墓主杨巨卿“通儒经,训诲童蒙,敬佛念经”。[22]又如李元阳《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记明将领唐时英(1496~1576)先祖为湖南人,长于研习儒家典籍,“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泸,遂世居曲靖之北关……甫十余岁,能属文,治《尚书》,日诵千言”。[23]以上种种皆说明,明代云南儒学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儒家经典成为必读之书。
二、社学、书院及学宫:明代云南儒学之演进
(一)社学的兴起
元代始设社学,学宫及书院设于府、州、县等,因远不能到学者,习社学。《明会典》卷七十八:“凡提督去处、即令有司每乡每里俱设社学、择立师范、明设教条、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较、择取勤效。”社学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明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弘治十七年规定“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得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入书院并无年龄限制,社学一般在十五岁以下,社学及书院均以基础教育为主。不同的是,社学承担德育教育,书院承担初等教育。嘉靖元年(1522)傅良弼《木密所社学碑记》:“滇民不惟不知教,而且崇尚异端,以害吾正。寻檄诸部毁其祠,改立社学。比至木密,其淫祠尤甚,其人信之尤笃……且乡党之学,士大夫所建,而朝廷因之。及州县学立,固为具文,而此独不废。其他聚徒讲学,皆足以为教于世,而不独此也。且木密所军民繁庶,旧无学校,使俊秀子弟有志而不获教,则玩岁废业,无所恃以为成者多矣。”[24]社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助力了民族地区百姓文化素质的提升。社学的命名通常成为学生的座右铭,如“遵礼”“敦信”“秉智”,《泰泉乡礼》卷三载:“社学之教,不专于念书、对句,务要教其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习礼乐、养性情。”[25]社学教育主要针对德育本身,而德育教育就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根本,少数民族地区的德育教育历来少有关注,社学的兴起可谓是重要补充,“建立社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道德,特别是儒家道德”。[26]
又如土官治理之地的姚安府亦曾大力提倡社学建设,《社学碑记》(1532):“辛卯(1531)建社学……兴举社学,以敷文教……建社学二十八所,为诸乡社学之首。”[27]明代社学的兴起是全民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也为清代儒家文化的扩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明代以前,云南地区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立、封闭的社会空间。虽自汉以来有受汉文化影响的历史遗迹出现,但影响力远不及学宫、书院及社学的促进明显,明代的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也使民族地区百姓逐渐接受儒家文化。
(二)书院的发展
明代云南所建书院66所,其中,景泰年间1所,弘治年间4所,正德年间5所,嘉靖年间11所,隆庆年间8所,万历年间9所,天启年间1所,崇祯年间2所,无明确年代25所,较为代表性的如五华书院(云南府)、龙华书院(浪穹)、凝川书院(浪穹)、秀峰书院(腾越州)、玉泉书院(赵州)、栋川书院(姚州)、龙溪书院(鹤庆州)、梅谷书院(晋宁州)、金华书院(剑川州)、桂香书院(禄丰县)等。明代较早的书院碑记是王臣撰写的《苍山书院记》(1499),记述了书院之沿革及陈设,“弘治十有二年秋八月,大理苍山书院成……前卫明德堂,后为尊经阁,下建升仙桥”。[28]大理苍山书院,又名苍麓书院,建于弘治十二年(1499),由御史谢朝宣(字汝为)建,正德、万历、崇祯各朝均增置学田。李元阳《源泉书院记》(1566)记大理苍山书院“舍宇狭隘,仅栖三十许人。郡邑两黉诸生四五百人,贫无庐者常三分之一”。可知,苍山书院始建之时,其院舍仅可容纳30余人,于是在嘉靖年间又修大理源泉书院。[29]
再如楚雄地区明代创立了松岩书院、龙冈书院、龙泉书院等,今存7块碑刻,如刘洙《创设松岩书院记》(1522)记述禄丰县所建松岩书院的情况,“距滇省几二百里,有属县曰禄丰。城东隅有文殊寺,其僧以轮回果报之说扇诱,愚庶趋附如市而莫之禁者数年。守大参刘公按部兹土,毅然毁其佛,擒其僧,而积痼之患遂绝。因其屋宇改为松岩书院,讲堂、斋房各三间,号舍、书屋各六间,择子弟之英俊者教之。”又如杨士云《新建楚雄府龙冈书院记》(1523)记嘉靖年间新建龙冈书院之沿革,“嘉靖癸未(1523),祝子以户部郎中来知郡事……既祠之且为书院,以养士矣……中为堂三楹肖侯之像,扁曰:人龙。左右为齐舍,各六楹,前为中门三楹,又为大门、为绰楔,扁曰:龙冈书院”。[30]云南龙冈书院始建于嘉靖年间,户部郎中参阅《楚雄府志》等文献,感叹“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于是命人重新修缮、增列贤人塑像,以待后人观仰。
嘉靖年间建造的楚雄龙泉书院经过历代更迭,延续至今。彭谨《龙泉书院记》(1562)“分命百户罗森辈董其役,经始于辛酉冬十一月,迄工于壬戌春正月。为堂三间,厦四间,八窗玲珑,诸门洞启。筑露台,凿月池,池之前为亭,覆以茅;亭之前为塘,砌以石;蓄而鳞,种而蔬,老树新花,杂植周布,宛然一城市山林矣。乃匾其额曰:龙泉书院”。龙泉书院建造于1561年,“盖将使合志同术,相观求益,庶不入于孤陋寡闻之弊。而其问学也,必如川之方至,泉之始达,日新不已,左右逢源”。隆庆年间,龙泉书院又经过重修,杨守鲁《重修龙泉书院记》(1568):“隆庆初元(1567)冬,首蒞威楚,惟楚称滇西巨镇,人文视东辅郁郁差弗著。郡旧有龙冈书院,近市嚣尘。寻废,徙雁塔山巅为南城院,又屹峙矗耸,俯瞰学宫,气淑罕锺也。佥宪彭君始改卜塔山之麓,距龙泉之阳,构堂疏池,选据名胜……”[31]书院的建设承担着培育人才、以化夷民的重任。与学宫稍有不同的是,书院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学宫大都可以上升为高等教育的范畴。书院教育以后,经过考试的诸生可以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32]
(三)学宫的设置
学宫作为儒家正统,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载:“古者,国家造士之所皆曰学,又曰学宫。后世以其庙祀孔子,故曰庙学,亦曰儒学。”[33]明代沿袭元代的学宫有11所,如云南府学宫,元至元间总管张立道建;洪武初年,西平侯沐英因旧址建庙学。洪武年间新设学宫有17所,如呈贡县学宫,洪武十六年建;正统十四年,知县何温重修。永乐间新建3所,嘉靖间新建13所,如大姚县学宫,嘉靖二十五年,知县王佩建;广通县学宫,建于嘉靖二十五年等。明代新建学宫62所,其所设立既可延续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又能培养人才、教化后辈。
元代设置学宫延续到明代的大都由于战乱被毁,明代统治者平定大理以后,实行了卫所制度,并且积极建造学宫、文庙等机构以树立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明代前期的驻扎将领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到中后期明显有所放松。云南处于民族地区,建立儒学正统地位不但有利于对云南等西南地区的统治,也可提升当地文人的文化素质从而进一步加强边疆治理。对于培养儒生之功用,童轩在《重修曲靖府儒学记》(1470)里有所论述:“自古王者建国,君民廉不以养士为先,而其所养又必以讲明斯道为要。向使道之不明,则处也其体无以立仕也,其用无以行,又奚用是学校为哉?”[34]研读儒家典籍,习孔子之道是为正统,学宫的建设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儒学传播更为重要。
然而,学宫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很多地区的学宫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如曲靖府学宫的修建就经历了百年之久,曲靖府学宫创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永乐元年重修。景泰五年,巡抚郑容重修。成化三年,巡按朱皑、知府张纯重修……丁亥三月,流寇屠城,复成灰烬”。[35]柯潜《曲靖府儒学记》载景泰五年(1454)重修时的场景,“功之序,先礼殿,次从祀之伍,次讲艺之堂、栖士之舍,以至庖湢既、库、燕处之所,百凡俱备。其材坚良,其制伉伟,其功枚密,视旧之庳陋,盖增倍蓰焉”。[36]成化六年(1470)又对学宫进行了修缮,童轩《重修曲靖府儒学记》:“成化四年冬……于指挥周祯、周琛得数十余弓肆,鸠工市材,选任曲靖、越州二卫指挥千户等官之有干局者经营萤作。其间别构讲堂于文庙东偏,前左右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奇,中为仪门。后堂五区,僎堂三区,与夫公廨、宿庐、庖福、库庾以区计者,凡八十有奇。”[37]学宫的不断重修,一方面反映了当地政府对儒学的重视,提倡重修之人多是巡抚、知府等官员,并不是县学教谕等人;另一方面,也是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直接体现。
再如石屏州文庙的修建,文庙于元至正间建,后于明洪武二十一年重建。《新纂云南通志》记“正统五年,学政王骥、景泰间知州任斌重修。万历间,知州萧廷对建尊经阁。天启五年,久雨,大殿倾仆,署州顾庆恩拓地重建”。周洪谟《石屏州庙学记》(1454):“国朝洪武二十一年,始复建庙学,岁久滋蔽。正统五年,今监察御史王公骥,时为是州学正,捐俸率诸生修大成殿及东西庑……景泰二年秋,知州任彬偕署学士王绍宗甃大成殿址,饰夫子像,并塑四配十哲。”[38]石屏州文庙的建设,先有大成殿及东西庑,后逐步增修明伦堂及居仁、由义二斋、棂星门、仪门等建筑。[39]
明代对学额的规定与前代明显不同,[40]《新纂云南通志》载:“永乐二年,云南土官张文礼等入监者二十八人,是后,滇、蜀土夷官民生入监多或至六七十人。十年六月癸亥,赐国子监琉球国、云南、四川民生怀德等一百三十六人夏布蓝衫、靴绦。”[41]明代,府学置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置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置教谕1人,训导2人以学宫(文庙)为署所,管理府州县学校。学额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木芹先生考察明代云南府学定额560人,州学840人,县学600人,卫所学额900人,总计约3000人。[42]有明一代,云南进士自洪武二十七年(1394)至崇祯十六年(1643),共有进士223名。其中,不少进士都有碑文传世,如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进士赵璧曾于成化二十年(1484)撰《重修大德寺碑》;同科进士杨一清于正德六年(1511)撰《游招隐山诗碑》;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李华于正德十五年(1520)撰《汪公修理城碑》等。
社学承担了德育教育,规范十五岁以下学子的思想品德,秉持儒家精神内核;书院教育选拔品德修养高尚学子继续学习儒家文化。社学还兼带培养没有设立县学、书院地区的学子,进行道德方面的普及教育。学宫则是各地通过层层选拔,品德良好、精通儒家典籍学子学习的场所,“社学+书院+学宫”的教育体系,非常完备,既增强了德育教育,又兼顾了初等、高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儒学碑刻所见儒家思想在云南传播的儒学史意义
(一)促进官学推广,加强中央联系
明太祖初定天下,即以儒术化成天下,命儒臣纂辑《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理学著作,将朱子之说颁示学宫,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明代儒学延续宋元以来的学术传统,中央与地方皆有定制。《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古代学制一》总论明代学制:“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学制详明,为历代最。其学科之扩充,学规之严密,皆较优于历代。中央学校则有国子监与宗学,地方学校则有府学、州学、县学、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都转运司儒学、抚按儒学、诸土司儒学、社学,此外尚有京卫武学、卫武学、医学、阴阳学等,而民间书院亦称极盛。”[43]
明代云南各州县学加速了府、州、县的学宫、庙学及书院建筑的兴建和修缮。自洪武年间开始,府学、县学就开始对学宫的修缮工作。自嘉靖十年(1531),州县学皆建启圣祠、世宗御制敬一箴亭及《注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云南地区还建立起以“尊经阁”为名的藏书楼。何邦宪《宾川州儒学记》(1524):“十二月乙丑,书院成,中为楼以藏书,名尊经阁,以备制也,前为重门,后为讲堂,翼以号舍,缀以庖福,楼楼堂堂,盖与学宫相为负揭。”[44]官方儒学以四书、五经为经典教之,明副都御史唐时英(1496~1576)《靖阳书院记》:“我思古人师于图书,列为卦畴,为《典》《谟》《训》《誓》,为《三礼》《六经》,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继绝学教万世无穷,譬如天地无不覆载,四时行而百物生”。[45]户部侍郎张志淳《重修儒学记》记蒙化府知府左正(1488~1556)倡导儒学:“守又好善经术士,受《易》《书》《春秋》三经于专门,可不谓学乎?夫学则明,明则智,智则用心衷,衷则循而整,丰而制,动而不扰,而得民与士殆其末已。”[46]
明代儒学兴盛,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有明一代共有261位云南籍文进士。[47]对比元代只有6位进士来说,明代儒学传播力大幅增强,学宫、书院等建设远超前代。如明洪武年间重修云南府学宫、建晋宁州学宫、呈贡县学宫等,弘治年间建昆明县学宫、宜良县学宫等,儒学作为民族地区与中央联系的文化纽带,在边疆治理、人才选拔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汉以来,中央政权就十分注重对云南地区的儒学传播,彭时《重修儒学记略》:“云南,古为要荒之地,自汉以来虽通中国,而夷习自若……迨我皇明改中庆为云南府,建府学于城西。天顺庚辰,太监梅忠见学宫敝陋,以次兴修,经始于辛巳四月,明年六月告成”[48]。
(二)兴盛私家著述,扩大儒学传播
与官方儒学相对应的是私家著述,亦称私学。明代官方经学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八股取士亦以此为标准。在官学之外,明代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激发了私学的兴盛。《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一《艺文考一》:“滇自炎汉张叔、盛览从学司马相如,受经归教乡人,许淑亦受五经教授本乡,为滇南文化渊源。厥后,彬彬多文学之士。元、明以来,于斯为盛。”[49]明代私家著述开始增多,《新纂云南通志》著录滇籍明代文人著作321种,[50]云南儒学著作绝大部分见于记载都是从明代开始,张志淳、杨黼、李元阳、兰茂、杨一清等文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明代白族文人杨黼(1370~1450)“好学,读五经皆百遍。书工篆籀,兼好释典,躬耕献亩,以供甘旨。注《孝经》数万言,引证群书,极谈性命,字皆小篆”。[51]杨黼撰有白文《山花碑》,作为白族文人的代表,杨黼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大理杨氏家族显赫,杨黼先人杨智、杨保在元明之际皆担任要职。杨森所撰《重理圣元西山碑记》(1450):“杨氏系九隆族之裔,世居五峰之下阳溪……连生祐,祐生甫,俱有德潜。甫生智,元末授元帅。智生保,辟为书史。乳养妹之子黼,以承宗祀。”[52]杨黼祖父杨智(?~1366)曾授元帅之职,养父杨保(?~1382)又“辟为书史”,后授元帅。《故处士元帅杨公墓志铭》明确记载杨智世系情况:“祐生甫,袭任万户,甫生三男,长曰智……次曰寿,生子曰保,养亲甥杨黼。”[53]杨氏为大理白族第一大姓,杨森、杨士云、杨景修、杨南金、杨金铠等人在白族文学史上有大量著作传世,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54]
明代文学家李元阳(1493~1580)编著《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并撰有120余篇碑志文。李元阳撰写了大量书院碑刻,并在书院任职,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宾川州秀峰书院落成,撰《秀峰书院记》;[55]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理文昌宫建成,作《大理文昌宫记》;[56]嘉靖四十一年(1562),作《剑川州重修儒学先师庙记》等。[57]碑记中多记书院之沿革,如《源泉书院记》(1563)记大理苍山书院“舍宇狭隘,仅栖三十许人。郡邑两黉诸生四五百人,贫无庐者常三分之一”。可知苍山书院始建之时,其院舍仅可容纳30余人,于是在嘉靖年间又修大理源泉书院。[58]李元阳重视宋以来的理学传统,他在《与邹颖泉大参》提及:“本朝续道统,自白沙、阳明二先生以来,贵省则一峰、东廓、念庵,此仆所愿学者。故于山水幽绝处,奉主作祠,以寓景仰之思。”[59]李元阳推崇理学,信中所举陈白沙、王阳明、罗应魁、邹守益、罗洪先等学者都是重要的理学家,“志于明道者,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重刻楞严会解序》)正是其学术思想的总结。《新纂云南通志》所收滇籍儒家类著作27种,绝大部分著作都与心学、理学相关,如涂时相《养蒙图说》:“是书以四字为目,始孔子陈设俎豆,终宋程伊川门人吕希哲公私不扰,共九十目,皆取自周至明堪以为人模范之事。”明代滇籍经学家中,白族文人杨禹锡曾担任大理教谕,著有《读易》《诗义》等。云南白族文人受到儒家文化浸染较深,以至谢肇淛《滇略》谓“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以右实之……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60]
(三)提升土司文化,增强儒家认同
明代的儒教政策,不仅为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加强了西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明代在云南地区共设置武土司和文土司443家,“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予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教其子弟,上然之”。[61]云南土司十分注重家族教育,他们将子女送到内地学习儒家经典,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62]《木氏历代宗谱碑》记明嘉靖年间土司木高授文职“廿玖世祖阿公阿目,讳木高,字守贵。都院工部札付授三品文职,移咨吏部题实授,赴京进贡,钦赏实授三品”。[63]木高(1515~1568),字守贵,号端峰,是明代丽江府第九代土知府,有《白沙摩崖诗》(1534)等诗作传世。[64]木氏家族中木青(1568~1597)、木增(1587~1646)也都是以诗文名世。如木增撰《妙明居碑记》等。又如明统治者在金齿司(大理)建立儒学,王直《重修金齿司学记》:“至元,以为永昌,建学以教其人,后毁于兵。国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军卫镇之。……岁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僖往教焉。始立孔子庙于中正坊之西,军民子弟皆来学。”[65]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金齿司开始设立庙学,余子僖任训导,余子僖卒后,由其子余谷榖接任,“穀字止善,祗慎好学,有志于古人。……宽厚有智略,亦孜孜学术。庶几古人所谓悦礼乐而敦诗书者,其能成贤才而美风俗可必矣”。金齿司有回族闪氏,出多位举人、进士。如闪继迪(?~1637),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曾撰《龙泉寺常住田碑记》等;闪仲俨,天启五年(1625)进士;闪仲侗,天启七年(1627)举人。[66]大理白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文人接受儒家思想,强化了儒家认同,使边疆与内地联系更为紧密。
何俊《澄江府科第题名碑记》(1483):“澄江,滇南之名郡,虽汉夷杂处,然山川毓秀钟为,人物英迈,豪杰忠厚淳笃不亚中原。自国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开设学校,而岁贡聿兴,永乐辛卯而科目联第,殆今百有余年,人益知重儒术,士益知慕圣道,文风大振。”[67]正如碑记所言,以汉族、彝族杂居的澄江府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明代的科举政策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
结 语
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云南,以儒家思想为纽带,以科举应试为途径,与内地紧密联系。明代云南儒学传统继承元代而来,文化政策、学制定额以及相关规范都为清代儒学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儒学体系完善,实现了“社学(德育教育)+书院(初等教育)+学宫(高等教育)”完善的教育体系,云南地区作为明代儒学推广的缩影,反映了明代儒学在云南等民族地区的成功,不但是与中央政权联系紧密的见证,还增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文化自信。石刻文献作为文化史、社会史的补充,为全面细致勾勒明代云南儒学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佐证。
注释:
[1]赵成杰.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2]杜瑜.浪穹县儒学碑记[M].[光绪]浪穹县志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3]连瑞枝.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290.
[4]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94-395.
[5]王瑞平.明清时期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48.
[6]中共保山市委史志委,保山学院编.[乾隆]永昌府志[M].宣世涛,纂修.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72.
[7 晋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晋宁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002.
[8]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306.
[9]杨成彪.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915.
[10]凤凰出版社编选.乾隆大理府志[C].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71)[A].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70.
[11]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2518.
[12]李其馨,陈钊镗,纂修.云南省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594.
[13]李其馨,陈钊镗,纂修.云南省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96.
[14]李其馨,陈钊镗,纂修.云南省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82.
[15]李其馨,陈钊镗,纂修.云南省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86.
[16]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85.
[17]刘文征.滇志[M].古永继,校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680.
[1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38.
[19]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189.
[20]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479.
[21]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511.
[22]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1215.
[23]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明代编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260.
[24]施珊珊.明代的社学与国家[M].王坤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272.
[25]连瑞枝.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345.
[26]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13.
[27]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193.
[28]师范纂修.滇系·艺文九[M].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29]杨成彪.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19.
[30]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452.
[3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67.
[32]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25.
[33]李春龙,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495.
[34]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25.
[3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25.
[36]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18.
[37]杨大禹.儒教圣殿——云南文庙建筑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133-134.
[38]廖国强.清代云南儒学的兴盛与儒家文化圈的拓展[J].思想战线,2019,(2).
[39]李春龙,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510.
[40]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94.
[41]李春龙,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467.
[42]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08.
[43]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27.
[44]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32.
[45]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68.
[46]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596.
[47]李春龙,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68.
[48]诏令及地理类著作的编订大多是官方行为,其中,诏令奏议类13种,方志类13种,山川河渠类3种等29种著作不计入私家著述。
[49]李春龙,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73.
[50]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759.
[51]侯冲,张贤明.杨黼家世及生平新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52]李元阳与杨氏家族交游甚广,《户科给事中弘山先生墓表》(1529)是为杨士云(1477~1554)所作的墓文,由杨南金篆额。杨士云,字从龙,号弘山,太和人,官翰林院庶吉士,是与李元阳齐名的白族文学家,有《杨弘山先生存稿》传世。《户科给事中弘山先生墓表》详述其事迹。杨慎、杨南金、李元阳等人与杨士云都有过密切交往,杨氏家族唐代由金陵入滇,本姓董,居喜洲。见苏焘:《明代白族诗人杨士云的“学人诗”及其诗史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53]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690.
[54]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691.
[55]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693.
[56]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193.
[57]李元阳.李元阳文集[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437.
[5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96.
[59]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M].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
[60]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51.
[61]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65.
[62]诗云:木氏渊源越汉来,先王百代祖为魁。金江不断流千古,雪岳尊崇接上台。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扫苔梵墨分明见,七岁能文非等才。黄乃镇.木府通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85页。
[63]宣世涛,纂修.中共保山市委史志委,保山学院编.[乾隆]永昌府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296.
[64]丁一清.回族文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30.
[6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29.
[66]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M].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78.
[67]据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的统计,明代云南书院数目应为78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来源:《学术探索》2024年第1期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