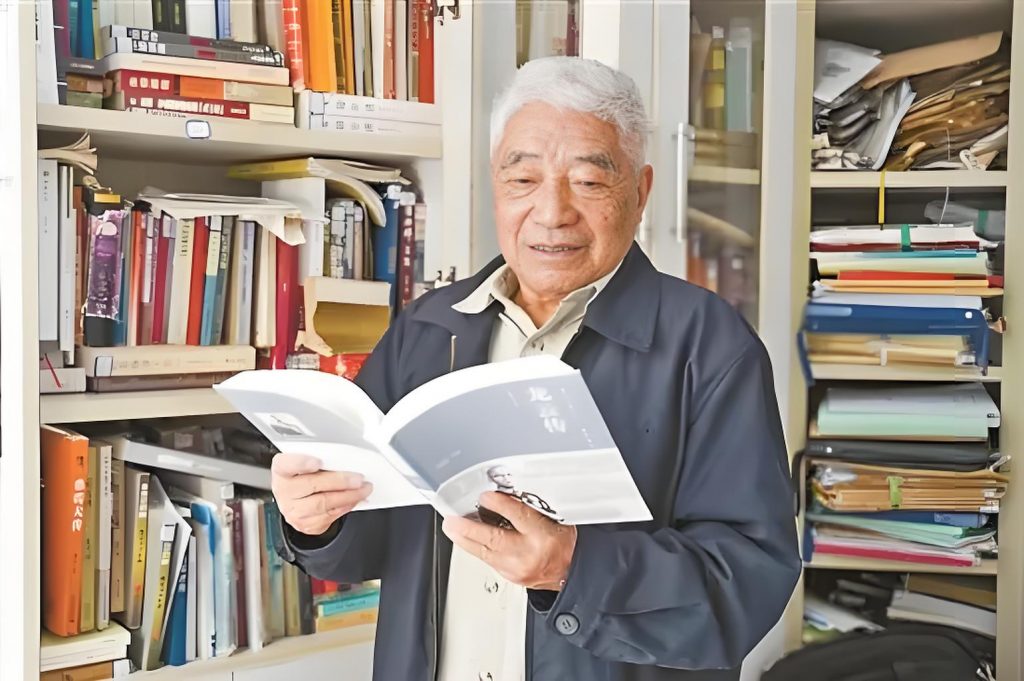
本文作者/谢本书
国家的边界是国家地理位置的界线,是国家主权实施范围的象征。祖国的概念是与国家的地理概念相联系的。因此,边界问题历来是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及其人民群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自然也应该包括国家与国家间边界形成问题的研究在内。
中国和缅甸两国之间边界的形成和最后确定(划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缅边界中国一侧绝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又全是少数民族地区。边界问题的形成过程中,还曾发生过轰动一时、震惊全国的中缅界务北段的片马事件和南段的班洪事件。直至1960年,中缅两国边界才得以最后确定。
1960年中缅边界的最后确定,是中国处理与邻国边界问题成功的典范。要正确地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就需要从中缅边界形成问题的历史源流说起。
一、历史上中缅友好关系是主流,近代以前边界问题并不突出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今天两国边境线长2186公里。纵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源于中国西藏,中国怒江的下游则是缅甸的萨尔温江。
缅甸的十多个民族与中国云南境内的景颇、德昂、佤、傈僳、哈尼、拉祜、阿昌、独龙、布朗、傣族以及克木人等是跨国而居的同一民族。互为近邻的地理位置和民族亲缘关系,为中缅两国密切往来提供了条件。
有文字可考的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距今已2000多年。公元1—2世纪时期,缅甸境内的部落,曾纷纷遣使来华通好,随后的缅甸各个王朝,如骠国、蒲甘王朝、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等,都曾多次派人来华,进贡方物。中国的历代中央王朝,亦曾热情接待了缅甸使臣,并给以丰厚的赏赐。尽管元、明、清时期,中缅两国曾发生过战争,但为时不长,战后两国关系迅速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成为中缅两国历史上的主流。
中缅两国交界地在历史上大体有个控制范围,即主权实施的范围,但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划定明确的边界界线。直到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当时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止缅兵的入侵和掠夺,才在腾越州边界一带建筑了八个边关,这就是:神护关(故址在今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万仞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孟弄山上)、巨石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铜壁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铁壁关(故址在今陇川县西北),以及虎距关、汉龙关、天马关(后三关,今在缅甸境内)。而直到清末,虎距、汉龙、天马三关仍在中国境内。李根源的父亲李大茂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率部实际查勘滇缅界务时,曾经考察了此三关遗址所在地,石刻尚存,只是“荆棘塞途,瘴毒尤甚,久无人行”而已【李根源:《雪生年录》卷1,1930年上海铅印本,第3-4页。】。这八个关及其以内(以东、以北)地区毫无疑问,处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八关以外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就是说,明代时期,中缅交界处中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是在八关之外,而不是八关以内。
就在明代筑八关之后不久,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陈用宾更筑平麓城于猛卯,并大兴屯田,主要以营兵任屯,“非营兵而愿屯者听”。又规定任屯者在最初两年内免纳田赋,自第三年起始按收获的十分之一征收【《滇考》卷下】。
很明显,设关、筑城、驻兵、屯田等一系列措施,都证明了明代政府已在这一带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统治。
直至近代西方列强入侵缅甸以前,中缅边界问题并不突出。虽然双方从未划定过边界,然而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地段的实际控制地区大体上还是明确的。
二、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与片马事件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终于吞并了缅甸,中缅关系遂演变成了中国与英属缅甸的关系。英国在占领缅甸以后,下一步的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与缅甸接壤的云南,以便能够从云南打开侵略中国的“后门”,或如他们所说:“为中国西南无限的市场打开一个后门。”【[英]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125页。】这样,中缅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边界问题突出了出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缅二千多公里的边界,出现了中缅边界北段、中缅边界中段、中缅边界南段三个地段的问题。
这里,我们先论说中缅北段边界问题。
中缅北段界务,实际上反映以片马为中心的中国腾冲及其以北地区的中缅接壤地区的界务问题,大约是从尖高山以北至江心坡一带。这是中缅界务问题争论的重点。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需要从片马说起。
今天的片马是云南省怒江傈僳自治州泸水县的一个乡,又称为片古岗乡(片古岗乡是原片马、古浪、岗房三个乡之合称)【现片古岗乡为泸水县下辖的片马镇,下辖片马、古浪、岗房等行政村——出版者注】。片古岗乡位于泸水县西部,高黎贡山西坡,恩梅开江支流小江上游偏东。东隔高黎贡山与鲁掌(泸水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相连,南、北、西三面与缅甸毗邻,有中缅边界北段第10号至第26号界桩17个,国境线总长为64.4公里,是云南省西南边防前哨之一。境内山峦叠嶂、森林茂密,南北最长24公里,东西最宽8公里。片古岗地区平面呈长方形。1961年缅甸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片马地区时,估算面积为153平方公里。片古岗地区人少地多,日照条件好,温度适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待开发的地区,自古有“片马无穷山”之称。
历史上的片马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小江流域,而不仅仅是小江流域的上游偏东地区。与片马地区相联系的是历史上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问题。包括片马地区在内,历史上的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南起北纬25°35′,与缅甸及我国的腾冲县相接;北至北纬28°15′左右,与我国的西藏相接;西到东经90°左右,与印度拿戛部落以及阿萨姆相接;东到东经98°30′左右,与我国贡山、福贡、泸水等县相接。具体地说,这一地区的范围由北纬25°35′、东经98°14′起,向东北沿高黎贡山的支脉狼牙山、姊妹山、茨竹地山山脊,至我国泸水县西南隅,沿高黎贡山山脊北土,至贡山县境折向西北,沿担当力卡山山脊上至西藏南隅,然后西南沿西藏山脉、龙岗多山脉、巴特开山脉至印度拿戛部落和曼尼坡接界处,由此向东溯更的宛江的一小段后,再向东循班多岭、卡桑岭、蛮龙岭、其董岭、盘蛮岭而至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交汇处的汤薤渡,再溯恩梅开江而上至石峨河注入恩梅开江处,再溯石峨河至尖高山为止。其间包括恩梅开江下游以东地区(即茶山、小江流域一带)、恩梅开江中游以东地区(即浪速地)、恩梅开江上游地区、江心坡(即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的地带)、坎底以及户拱河谷等到地。【关于历史上中缅边界未定界四至范围,可参阅下列资料。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永昌府文征》记载卷25);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1931年刊本);尹德明等:《云南边界勘察记》(1933年刊本);张维翰:《拟陈滇缅界务意见书》(未注明刊本年代)等。】总面积略等于我国浙江省。历史上的片马问题,通常与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问题紧密相关。这一地区,“为川、滇、藏之屏蔽,其形势诚所必争”。【《宣统政纪》卷53。见《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827页。】
自古以来,片马地区就是中国领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族人民在这里开拓了祖国的边疆。片马属我国版图,至迟在元、明时期,即已设官治理。还在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政府借口“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从而取得了“商订通商章程”以及派员“在滇游历调查”的权利。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再次强迫中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其中规定“会同勘定”中缅边界,“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7、卷67,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新纂云南通志》卷165。】。这就初步打开了中国的“后门”,实现了其侵入中国西南边疆的野心。
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侵略者又借口一个英国人被野人山(在迈立开江以西)的傈僳族烧死,派兵进占傈僳族居住的野人山、江心坡的麻阳、垒弄等寨,烧毁傈僳族居住的汉董、户董等寨。这是英国入侵野人山、江心坡的开始。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又派兵占领了江心坡以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居住的昔董、马董等地。英国的侵略活动,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抵抗。清政府眼见英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又见我国各族人民群情激奋,乃令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国政府交涉滇缅边界问题。光绪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与英国外相劳思伯利(Rose-bury)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这个条约的内容十分广泛,除规定英人可以在蛮允设领事、开放蛮允和盏西的商路及货物减税权,还对中缅界务作了全面的规定,其中第四条,关于中缅北段界务,作出了如下规定:“今议定北纬25°35′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新纂云南通志》卷166】这里所说北纬2535’,是指北纬25°35′、东经98°14′之尖高山(在腾冲之北)。这是中缅北段未定界第一次见诸条约规定。但是这个规定笼统且含糊,埋下了片马问题发生的伏线。不过,薛福成当时曾向清政府表示:“野人山地除八莫外,赤道北24°以上皆是,向不归缅,现拟与英分界。”【薛成福:《滇缅划界图说》之“十论滇缅界务书”】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日(1898年7月28日),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Donald)就中英勘分尖高山以南界线的交涉照会清政府。照会说:“上年十二月间,有华官带兵二百名进入恩买卡河北境内,请转饬该处地方官于恩买卡河与萨尔温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干预地方官治理之举。”【新纂云南通志》卷167】这里所说的恩买卡河就是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就是怒江,中间的分水岭就是高黎贡山。这就是说,英国在事实上提出了要以高黎贡山为中缅北段的边界线,以达到其侵占中缅北段全部未定界土地的要求。清政府不了解英国照会的真实意图,仅以“咨行云贵总督酌核办理”应付了事。
英国照会所说“华官带兵二百名进入恩买卡河北境”一点,确有其事,但那是中国地方当局行使自己正当的主权。据记载:“光绪二十年,适片马、江心坡普蛮有喇浪、中干二邑,争持盐水,互杀不休,前来向六库土司请援。经六库土司段浩命其胞弟段济,率兵往攻,已克服恩梅开江东西村落二十一寨,盐水取为官有,每年终按户征收黄莲门户,每户得莲二斤。”【段成钧纂:《泸水志》,1932年石印本,第40-41页。】应该说,这件事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片马、江心坡地区所行使的主权。
英国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以恩梅开江和怒江分水岭(即高黎贡山)为界的侵略阴谋,竟企图诉诸武力。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英军数百人和缅军一千余人,从密支那向东北进入北纬25°35′以北地区,抵当时中国管辖的拖角等地,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对沿途村寨实行“招安”。光绪二十六年正月(1900年2月),这支侵略军进入我腾越厅所属景颇族、傈僳族、汉族人民居住的滚马、茨竹、派赖等村寨抢劫掠夺,激起我边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腾越厅得到报告后,即派人前往劝阻。英兵置之不理。当时派赖寨的甘稗地,驻有土守备左孝臣、土千总杨体荣率领的土练,他们基于爱国热情,积极进行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左孝臣为世袭腾冲县所属明光宣抚司土守备,其管辖领地,东至大塘,南至北石岩,西至石坡鲁必、九角塘寨,北至茨竹等地、习降小江十八寨。【《左孝臣墓碑》。左孝臣墓在今云南腾冲县明光区麻栎乡大花山腰,墓前有碑。】正月十四日(2月13日),英方入侵司令三次派翻译对左孝臣、杨体荣虚伪地说:“彼此和好,勿开边衅”;但当日晚上,英军偷袭甘稗地,将滚马、派赖、茨竹、官寨、痴戛等地村寨掠烧一空,威逼附近村寨居民投降。左孝臣、杨体荣率领土练500余人,组成先锋营,执刀、戈、矛、弩弓,英勇抵抗,浴血奋战。第二日下午,因敌人众多,武器精良,各族边民伤亡达140多人,其中牺牲80余人。【尹明德等:《云南北界勘察记》卷2,1933年版,第9-10页。】左孝臣身中八弹,为国捐躯。
事件发生后,腾越镇总兵张松林、署腾越同知杨均“闻警,派兵往援,并饬不准越界追击,英军始退出界外。适提臣冯子材查阅营伍至腾,臣即电请提臣督同镇厅妥为布置防务,绅民亦请留提臣暂驻腾越,以资镇慑”【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52,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英军退至拖角后,腾越厅致电密支那府,抗议英方派兵烧杀抢掠中国内地及其居民,并根据伤亡的人数和人名,详细造册。对此,英军置之不理。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竟致函清政府说,两国发生冲突的地方是在“缅甸界内”,并且威胁说:“边界迤西倘遇他国兵队,不能不立行驱逐。”此后界务交涉,文牍纷争不绝,都未取得什么结果。英方坚持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所谓“天生极妙界限”,企图把“暂时从权之界”变为“滇缅确实之界”,并进行威胁:“近三年来,英员于该处情形,略悉梗概,查明最妥易识之天然界线,乃系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河之分水岭,此界先视为暂时从权之界,现奉本国政府训条,转致贵国政府,如之定妥,于未定妥以前即拟视为滇缅确实之界,若不守此界,滇省派兵逾越,恐有与英兵相触之祸。”【档案资料,未刊。参见拙文《片马问题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
清政府坚持不同意英方的要求,主张双方派员会勘中缅边界。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日(1905年3月7日),清政府委派署腾越关道石鸿韶与英方委派的驻腾越领事列敦,在腾越的古永街相会,上界查勘,到五月初勘毕。此次查勘,石鸿韶坚持“现管小江边”,因而应顺小江边直勘至小江源,抵板厂山。列敦则要由明光河直上高黎贡山,循岭北往西藏,凡水归龙、怒二江者,概归滇;凡水归金沙江者,概归缅【龙江、怒江分别指龙川江、怒江。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恩梅开江、迈立开江。】。列敦的意见,实际上是要在尖高山以北,以高黎贡山为界。这样,片马、岗房、鱼洞、茨竹、派赖等寨,就要划入缅境。石鸿韶据理以争,出示有关证据,说明这些地方归中国管辖,中国委任的抚夷官有道光年间的兵部扎付。列敦理屈词穷,表示愿由缅甸政府出印洋4000元,作为补偿,交与中国官员转发各土官;而且,缅甸政府还愿出印洋1500元,援照猛卯三角地成案,永租这块土地。清政府当然不能同意。然而,列敦以石鸿韶愚懦可欺,所有勘察,事实上全在中国势力管辖范围内进行,而且大部分还在尖高山以东、分水岭垭口以南、高黎贡山以西打转。这种“会勘”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对会勘所绘之图,双方注明,彼此无划定之权,不能作为划界之凭据。列敦所提出的界线,后来称为“紫色线”或“高黎贡山线”,即以高黎山分水岭为界。石鸿韶所绘之界线,后来称为“绿色线”,大体上是以小江为界。虽然石鸿韶提出的“绿色线”与列敦所提出的“紫色线”不同,即将片马、派赖、茨竹等地划入我国境内,但是小汪以外的土地却完全置之不顾。这样,“国人咸咎石鸿韶勘界失地,贻误边疆,内外滇人,一致呼吁。石因此革职”【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1931年腾冲版),载《永昌府文征》记载第6册,卷30。】。
英国政府根据列敦的报告,要求清政府以高黎贡山线(“紫色线”)为界,以便“和平商结”。清政府则认为,列敦、石鸿韶的会勘,“直是分割华境”,因而要求“另行派员勘办”。此后,清政府外务部又提出了“蓝色线”,此线实际上以恩梅开江为界;云贵总督依据洋务局的意见,提出了“黄色线”,又称“扒拉大山线”,实际上是以恩梅开江以西之扒拉大山为界;此外,1900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还提出过一条“红色线”,此线介于小江和恩梅开江之间。蓝、红、黄、绿、紫五色线,即清末提出的中缅北段边界的“旧五色线图”。
这一时期关于中缅北段边界会勘与交涉的范围,已经不是薛福成所说“拟与英分界”的“野人山地”。也就是说,已不是条约所指的北纬25°35′之北的不属于缅甸的土地,而是由中国治理的并为当地土司、土官所世守
的地区。英国侵略者不仅侵占了北纬25°35′以北的不属于缅甸的土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侵略高黎贡山以西确实属于中国的土地。清朝方面提出的“五色线”中的红、黄、蓝、绿四线,没有一条是画在恩梅开江以西地区;而英国方面提出的“紫色线”,却绕过清政府所治理的小江流域,伸入到中国内地,将线画到了高黎贡山上面来了。尽管如此,中缅北段边界仍未划定,悬案仍未改变。
宣统元年(1910年),保山县属登埂土司与所辖片马地方的汉商徐麟祥、伍嘉源等发生的冲突,是片马事件的导火线。
徐麟祥,今腾冲县明光区徐家寨人;伍嘉源,今腾冲县城关人。他们历年在片马一带贩卖杉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鸿韶勘界至片马,令登埂土司整理“团务”,登埂土司为此在片马设立分团局,并委徐麟祥为片马团首,代土司在片马地区收杉板税。其后,由于徐麟祥因事被土司革职,怀恨在心,以及登埂土司的杉板税极大地影响了贩运杉板的利益,因而徐麟祥约同伍嘉源、段有贤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保山县控告登埂土司“倚官虐民,加抽官板”。当时保山县判令土司不准再收杉板税以及“水租门户”。徐等胜诉,向茶山一带居民摊派讼费银265两,并开始拒绝向土司纳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1908年3月14日),登埂土司段浍派段澍率兵前往片马,徐麟祥等动员当地居民一百多人至片马大田坝持械阻抗,段澍人少,不敌而回。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9年11月6日),土司段浍又领兵去片马,徐麟祥再次纠集小江片马一百余人前往阻拦。双方发生冲突,烧毁上片马栋姓草房6间。徐麟祥、伍嘉源、段有贤等策划,登埂土司若再来管理,将盗窃茶山各寨之名,“往投洋人”,以求保护。于是,由段有贤刻“禀词”,派人前往密支那投递,结果送到昔董,随即由缅甸政府送到英国驻腾领事处。“禀词”要求英缅当局“伏乞做主,赏准到地查明”。这个“禀词”,虽然向英缅当局求援,却并未涉及中缅边界问题。更何况,“禀词”谈不到有任何法律效力。英国却认为有机可乘,准备以此为借口,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英人无理指责登埂土司带兵过界“烧抢”,要求“赔偿缅民损失”。云贵总督为此指示,片马“原隶云龙州,后改归保山县,应征额粮二石四斗,为流官直辖之地,有道光年间奏案可稽,粮由登埂代征,故片马年纳登埂门户税银五十两,又抽收冈银一百两”。因此,登埂土司与片马居民之间的纠纷是我国内政,与英国无关,而且出事地点,远距边界七八百里。【档案资料,未刊。参见拙文《片马问题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
1910年11月下旬,英国决定派驻密支那府官郝滋(Hertze)上校,亲自率兵一千余人,驮运弹药骡马二千余匹,由弗罗(Flow)上校指挥,到昔董待命。英国驻腾越领事娄斯亦到昔董,共同会商侵略事宜。1910年12月26日,英方先遣部队百余人,驮马五十多匹,驮载弹药、锄、锤等物,沿恩梅开江进抵拖角,并在拖角建筑储粮仓,抢修道路后,向片马进发。三天以后,英军大部队二千余人,驮马二千余匹,以及修路工人、赶马工人四百余名也相继来到拖角,并经盐井坝、把仰、毛绞,渡小江至独末、笼蚌、官寨、噬戛,再东渡小江,于1911年1月4日抵达高黎贡山西麓的片马,设营驻兵,实施军事占领,并分兵驻扎鱼洞、岗房。同时,英国侵略军焚烧了在片马的汉学堂,赶走了教师姜光耀。英人记载的情形是:“英兵由缅甸出发,经两月之久,中途小心惕虑,怕遇抵抗,沉着向片马推进。一面又听得谣言说:中国要打仗。实际此谣言仅由一品性谨慎之中国教书先生所流传。英兵到时,请此乡学究出面。此乡学究从容不迫,待半点钟之后,方缓步出来,鞠躬如也的见英官,对之曰:‘我们要你即刻离开此地。’乡学究应之曰:‘唯。’即束装跨过片马,回中国而去。英军遂进片马,占领其地。”【杨体仁:《英人经营滇缅边境之史实》,《永昌府文征》第7册,卷36,第7-8页;华金栋著:《缅甸极边》(1921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片马事件”。
英军入侵片马遭到当地傈僳族、景颇族人民猛烈的反抗,为首的是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勒墨夺扒曾与片马各族人民一道,多次进行反英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二年(1910年),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曾两次以贿赂收买勒墨夺扒,都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一次英军大规模入侵,更激起了勒墨夺扒的愤恨,他毅然联络头人姚中科,率领各族边民,与英军进了“誓死不屈”的斗争。当英军进入古浪大寨时,勒墨夺扒领导的一百多人的抗英队伍,身披蓑衣,手持弓弩,伏击于古浪寨旁的丛林中,打死了一名英军军官,英军狼狈南逃。【见《片马烽火》编写组《片马烽火》,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英国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入祖国内地,舆论沸腾,人民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云南省城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以为政府后援,云南省咨议局推举周钟岳、李曰垓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力争收回七府矿权。【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云贵总督和清政府都向英国当局提出了严重交涉,但却未能派兵前往片马。坚持在片马地区斗争第一线的是怒江两岸的傈僳、景颇、彝、白、汉等族边民,他们汇集了四百多人的抗英弓弩队配合泸水县属各土司派出的民团一百多人作战。
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弓弩队分南北两路向片马挺进。由南路进军的二百多人,登上高黎贡山,经过古炭河直奔片马垭口。从北路进攻的弓弩队也有二百多人,凌晨碰上英军巡逻队,傈僳族神箭手褚来四射中一名英军军官的眼睛,英军乱作一团,被迫退走。
由于清政府只提出外交抗议和严重交涉,未派军到片马前线,英军未遇到严重阻力,因而在占领片马、古浪、岗房以后,从1911年底到1913年间,先后派兵向北占领茶山地及俅夷地,并于1913年由坎底(葡萄)分兵两路,一路向东北,直趋窝门、木刻戛,进入独龙河下游;另一路向东侵入拱路、扩劳铺。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旋即被推翻。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派遣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到滇西,处理滇西问题。李根源又遣怒俅殖边副委员长何泽远率殖边队进入独龙河下游与恩梅开江汇合处的乐玉池,同英军遭遇,双方激战甚烈。殖边队无后援,虽经苦战,仍处劣势,何泽远战死,军队全部退回贡山。【《民国初年殖边队进驻怒江碑文三篇》,见《怒江文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第2辑。】这是英军入侵片马后遭遇到我正规军的首次严重抗击。至此,郝滋率领的英军控制了片马、坎底(葡萄)等广大地区。这就是说,英军用武力在事实上强占了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大部分地区。到1914年,英国在坎底一带设立葡萄厅、拱路厅、孙布拉蚌厅,又在小江的拖角设立拖角厅(相当于县级),以管理恩梅开江下游以东地区(即之非河与小江流域之地)。拖角厅的辖区,东到高黎贡山的片马垭口,东南到滇滩的板瓦垭口、明光的大垭口和茨竹垭口,南到石山峨河,西到恩梅开江,北到小江口项高山,东北到板厂山。英军还在片马、拖角、尖高山等地设立兵营。英军头目郝滋上校因侵略有“功”,被英王授予男爵称号,驻扎坎底,成为这一地区的行政长官。【《傈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片马事件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片马事件以后,虽然英国在片马地区设立兵营,实行武装占领,并设官治理,然而,由于云南各族边民的反抗,全国人民的抗议,加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不承认英军对片马的占领,这就为我国后来最终收回这一地区打下了基础。
三、中缅中段界务问题与猛卯三角地
中缅边界中段,根据1894年《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其分界线为“循南莫江而行,至南莫江分开处……”,这样云南西部南畹河和瑞丽江合流处的南畹河三角地区,因其地近猛卯,又称猛卯三角地,涉及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公里,自然归中国所有。三角地气候属亚热带,居民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主。
这个三角地带元代隶属于麓川。元代至元十三年(1267年),“立为路,并隶于金齿宣抚司”【《明史》卷340,《麓川传》考证。】,并多次向元政府“贡方物”【《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元史》卷34《文宗本纪三》。】。到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领有元代平缅、麓川两路。明代,思伦发继任麓川平缅宣慰使后,曾不断对外扩张,形成对明代中央政权的威胁。因此,明政府曾任命兵部尚书王骥率部三征麓川。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撤销麓川平缅宣慰司,改置陇川宣抚司。到万历初年,猛卯脱离陇川而别立土司,从这时起,猛卯三角地就是猛卯土司辖地的一部分。
有清一代的重要地图,如康熙年间(1662—1722年)官方出版的《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元年(1736年)出版的《云南通志》中所附《云南全省舆图》及《永昌府舆图》、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续成的《大清一统志》附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云南全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兆洛绘制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同治二年(1863年)官方出版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和光绪二十一年(1985年)出版的《皇朝直省地舆全图》等,都把猛卯三角地无例外地划在我国界内。【余绳武:《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见《中国边疆研究通报》(第二集,云南专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不断向云南一侧扩张,陇川、猛卯一带距八莫较近,首先受到严重威胁。早在1889年,猛卯土司辖境附近的盆干、后崩等寨已为英军占据。接着,英军擅自修筑一条从八莫经天马关内“山梁上”直通南坎的公路。天马关本来在我国境内,英国企图以此将猛卯三角地据为己有。1894年,在伦敦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答允由八募至南坎各路中之最捷一条大路,经南畹河之南中国一小段地内,除中国商民与土人仍旧任意行走外,亦可听英国办事官员及游历之人行走,并不阻止;英国如欲修理此路,或设法改筑,可臻平稳,告知中国官后便可动工办理;又有须保护商贾或防偷漏等事,英国亦可筹备办理;又议定英国之兵可以随便经过此路……”这样,英国侵略者在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又以条约形式巩固和扩大其在猛卯三角地的权益。条约中所谓“南畹河之南中国一小段地内”,便指猛卯三角地而言。同一条约还规定:“以蛮秀地方及天马关、欣隆、拱卯各村寨归中国”,明确地说明猛卯三角地归我国所有。
1897年2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缅条约附款》(《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续议附款》),其中第二条规定:“……南畹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濒南莫江支河及蛮秀岭之垒周尖高山,从此尖高山遵岭东北至瑞丽江,此段地英国认为中国之地,惟是地乃中国永租与英国管辖,其他之权咸归英国,中国不用过问,其生年租价若干,嗣后再议。”
从此以后,猛卯三角地便以“永租”名义由英国强行占领并管辖。“租金”在1899年确定为每年印币卢比1000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缅甸,猛卯三角地亦为日本占领。1945年在滇西缅北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收复了猛卯三角地,一度成立了“光复乡”。但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在英国的迫使下,将“光复乡”撤销,猛卯三角地仍由英国占领。猛卯三角地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又悬了起来。
四、中缅南段界务与班洪事件
中缅界务南段,主要指从南卡江起到孟定工隆渡的一段边界,其地主要在阿佤山一带,大部分是佤族聚居区。阿佤山区是云南西南的边境屏障,位于临沧、普洱地区和缅甸接壤处,在澜沧江以西和怒江以东,为怒山山脉的南部余脉。这里崇山峻岭连绵起伏,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于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长,而且,金、银、铅等地下矿藏也较为丰富。
英国完全占领缅甸以后,即不断向云南方向扩张。在1894年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对阿佤山区的中缅边界作了规定。其中第三条说:“……由此循英国所属之琐麦与中国所属之孟定分界处之江而行。仍随此两地土人所熟识之界线,至界线离此江登山处;以萨尔温江及湄江(即澜沧江)之支江水分流处为界线,约自格林尼址东经99°(北京西经17°30′)、北纬23°20′,约至格林尼址东经99°40′(北京西经16°50′)、北纬23°,将耿马、猛董、猛角归中国。在格林尼址东经99°40′(北京西经16°50′)、北纬23°处,边界线即上一高山岭,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岭向南而行,约至格林尼址东经99°30′(北京西经17°)、北纬22°30′,以镇边厅地方归中国。然后其线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顺南卡江而行,约过纬度十分之路,以孟连归中国,孟仑归英国。”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方面在中缅界务北段作了较大让步,作为交换,英国在中缅界务南段方面不能不有所收敛,因此英国撤销了一度提出的对车里(景洪)、孟连、镇边厅的无理要求。英国对此并不甘心,又寻找借口要求改订。1897年签订的《中缅条约附款》,虽然作了有利于英缅当局的修订,英国从中国手中夺去了科干等地,然而阿佤山的边界线,仍然维持了1894年条约规定的状况。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条约文字实际上只指出了边界的大致走向,内中有诸多的矛盾,难于落实。如约文中经纬点与分水岭位置的矛盾,与山名实际位置的矛盾,自然界线与政区界线的矛盾等。【张振鹃:《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研究通报》(第二集,云南专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从1899年到1900年,中英双方对中缅界务南段进行会勘。约文本身的矛盾在会勘中暴露了出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结果,先后提出红、黄、蓝、绿、紫五条分界线。
英国代表斯格德提出了两条线,一条是红色线(自拟线),另一条是绿色线(拟让线)。
中国代表刘万胜、陈灿也提出了两条线,一条是黄色线(根据驻英公使薛福成的草图为依据的拟划线)和蓝色线(拟让线)。
清政府外务部也拟出了一条界线为紫色线(部示线)。
这“五色线图”,因为差别较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遂被拖延了下来,并导致了“班洪事件”的发生。而酿成班洪事件的直接起因,则是英国的“缅甸有限公司”对班洪地区炉房银矿的垂涎和掠夺。而班洪地区即使按照未定界的划分,亦属中国管辖范围。
炉房是班洪、班老、永邦三个佤族部落共管的银矿。清初吴尚贤曾在这里开设茂隆银厂,年产纯银13万两。英国“缅甸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伍波朗,曾潜入炉房探察,并以每驮英洋十元的重价收购炉房矿渣。经过化验,炉房矿渣含银高。伍波朗为达到夺取炉房银矿的目的,用金钱物质收买边境头人班弄的马美廷(回族)、永邦的小麻哈(佤族)、户板的宋钟福(汉族)。由这三人出面与伍波朗签订了一个《开办炉房银矿办法》。
条约签订后,伍波朗唆使小麻哈等人以重礼引诱班洪、班老部落首领参加开矿活动,遭到严词拒绝。班洪等部落首领表示坚决反对英人侵地盗矿,并准备武力反抗。英国侵略者眼见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遂与小麻哈、马美廷、宋钟福等人策划,准备以武力攻占炉房,掠夺整个矿区。
伍波朗为此取得了英印殖民政府的支持,’从印度调来约千名雇佣军,拉拢麻栗坝土司杨虎臣,提供一千匹骡马将腊戍的军需物资运到滚弄江沿岸,又由宋钟福提供一百多头黄牛将户板的粮食运到滚弄江边。在党阳修建飞机场。沿滚弄江一带驻有雇佣兵约二千人。
1934年1月20日,英军以正规军250人为先头部队,自户板开出,经过孟混、班孔、班谷,占据户算、南大、金厂、炉房等地,构筑工事,建筑营房,运送工人开路,作长久占领之计。接着,英军二千人入侵班洪,强行督工采掘矿砂,运往老银厂冶炼。
英人又进一步指使马美廷向班洪王胡玉山第二、班老王困鄂及班老困刚锡龙散勐等人送礼诱降。这三家均世代看守中国银山,表示绝不违背祖训,要誓死保卫银厂。“是时班洪王痛愤英人无端侵略,遂召集作佤兵千余,保护矿厂,以拒英兵。”【余汉华:《英法两帝国主义夹攻下之西南滇边》,《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版)。】对于英国人所送财物,“坚不受”【石觉民:《木里与班洪丛谈》,载《边事研究》卷2。】,决心进行战斗。
班洪王一面召集民团准备战斗,一面派人分头到绍兴、新地方、公鸡、塔田、官中、蛮国、嘎喜、莫刊、弄垮、敢色、班老、永邦等部落送信,召集十七王开会,统一抗英行动。十七王接到班洪王的告急信后,除向各级政府报警外,很快齐集班洪,唯永邦王未到。在稍后各王发出的《告祖国同胞书》及《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伊斯兰先生》的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们说,阿佤地区,“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定边疆,迄今数百年,世及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即现存历朝颁给印信,可资凭证”。近日,英人“劲军千余,新式武器均备,明则探矿调查,遮盖我祖国人之耳目,淆乱世界之公论,暗则占领我班洪、炉房等处银矿,以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腕,无所不用其极,必得我全作佤山地,奴我作佤山民而后已”。并且发誓说,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告祖国同胞书》,载《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作佤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阿佤山部落首领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书》,转见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诸王会议,无不义愤填膺,对永邦小麻哈(永邦王之弟)引狼入室,甚为愤怒;他们一致议决,先打永邦、蛮和,杀死小麻哈,再对付英国人。会议估计可集结佤族武装士兵2000~3000人。因此决定兵分三路:新地方、公鸡、塔田、班老等攻打蛮相;蛮国、官中、小公鸡等攻打永邦;班洪、弄垮、嘎喜等攻打丫口寨、金厂坝。与会者歃血盟誓:如哪一路不执行上述决议,罚3亢(75两)金子、3驮银子、3头大象给其他两路。
佤族同胞的爱国呼吁,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映。驻普洱的云南第二殖边督办公署派委员到班洪,赠送火药等作战物资,鼓励边民保境爱国。镇康县长、勐董土司、澜沦县政府也分别给班洪地区边民物质支援和道义声援。
英国向班洪地区侵略的消息传入内地,舆论沸腾。在昆明有二十多个民众团体和部分爱国人士成立了“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动员人民从各方面声援班洪地区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并在各县成立分会。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云南学生和各界人士,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组成了“划界促进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援班洪事件的反帝浪潮。
在声援班洪人民斗争中,出现了“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的组织,为首的是景谷县傣族爱国志士李占贤。李占贤激于义愤,赶到普洱,向云南第二殖边督办杨益谦请缨出征,杨益谦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支持。李占贤得到杨益谦的支持,即倾家之所有,拿出10万现金作经费,组织“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李占贤向沿边各县发出组织义勇军的信息,迅速得到景谷、景东、石屏、缅宁、双江、耿马等县多人响应,先后有一千四百多人参加,遂组成“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指挥部”,李占贤自任总指挥官,苏右卿为副总指挥官。指挥部下设参谋、政治、秘书、军需、军医、副官等6处,分编5个大队,共有兵员约2000人。这支义勇军除汉族、傣族人员外,还有佤族、拉祜族、彝族、布朗族人民群众参加。
5月25日,义勇军赶到班洪边界信呵,得到班洪王和班洪地区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义勇军进驻班洪后,经过调查,得知英军入侵我阿佤山区域的兵力已达2000余人,大部为英军军官指挥的雇佣军,主力800余人驻扎在炉房矿区,其前锋200余人已深入到班老附近要隘丫口寨。根据这个形势,义勇军决定先打丫口之敌,协攻两翼之敌,最后进攻炉房正面之敌。
5月30日拂晓,义勇军五个大队全面反击开始。四大队彭季谦部先攻左翼,五大队杨春珊部再攻右翼,李占贤率一、二、三大队及班洪民团直接进攻丫口寨,总计投入兵力(包括义勇军和民团)达2200人。我军勇敢冲锋,激战一日,英军受挫,放弃丫口寨及上、下班老,退守炉房。此役毙敌五六十人,我方战死16人,伤30多人。
第二天(5月31日),班洪王代表张万美、义勇军代表李士相在公明山召集绍兴、别列、敢赛、光宗、蛮国、莫列、霞勒、霞岛、塔田、蛮回、贺猛、莫弄、夷勒、公己、班老等十五王举行了联席会议,订立了抗英盟誓。盟誓明确规定,各王永远服从中国政府,炉房厂地为中国所有,他人不得侵占;义勇军与各王在抗击英军斗争中相互支持,不得投降英国或不服从中国政府命令,否则由各王共同诛灭之。
义勇军在班洪地区各王和各族边民的支持下,于6月6日夺取了炉房。随后,战争中有胜有负,然而终于将英国侵略者赶出了班洪地区。
“班洪事件”体现了中国各族边民捍卫祖国领土的不可屈服的精神。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中英双方都感到解决中缅南段未定界的迫切性。到1935年,双方又派出代表,并同意由瑞士陆军上校伊斯兰为中立委员,参与勘界。然而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斗争。英国却竟于1940年7月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给中国施加强大压力。中国政府被迫于1941年6月18日与英国签订了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这条界线称为“一九四一年线”。根据这条线,阿佤山区约3/4的地区划入英属缅甸,曾经武装抗英入侵的沧源班老地区和西盟西部南锡河以东的一片地方也划给英属缅甸,而中国只保留了阿佤山约1/4的地区。然而这条线尚未勘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于是“一九四一年线”事实上仍然作为未定界而拖了下来。
五、中缅界务的最后确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行的和平外交和睦邻友好的政策,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解决,奠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我国周恩来总理参与创导和制定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进一步解决邻国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说:自从中缅“两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独立以后,特别是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创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以此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之后,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两国政府一贯珍视两国的传统友谊和维护两国独立和亚洲和平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确定了互谅互让和友好协商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日)】。
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0年1月28日在北京签字,2月19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5月12日经缅甸联邦总统批准,于同年5月14日在仰光互换批准书】。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签字,12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12月29日经缅甸联邦总统批准,于1961年1月4日在仰光互换批准书】。这样就完满解决了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缅边界条约》全部划定了中缅未定界线。在确定边界线时,本着友好协商、互让互谅的精神,既要考虑到历史上传统的习惯线,也要考虑到片马、班洪地区曾掀起过反英入侵的民族感情,还要对某些不合理的地段进行局部调整。这样,在中缅界务北段,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在中缅界务中段,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划给缅甸;作为互换,在中缅界务南段,将班洪、班老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归还中国。接着,在1960—1961年间,两国对中缅边界全面勘察定界,树立了永久性界桩。《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及其随后的勘界,成功地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为此后与其他邻国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为了庆祝边界条约生效,中国政府通过缅甸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20万缅甸居民赠送240万米花布和60万个瓷盘;缅甸政府则通过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00万中国居民赠送2000吨大米和1000吨食盐。
中缅边界的最后划定,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原载《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版。















暂无评论内容